[第八屆散文組佳作]陽明醫學六-林佳亨《有病》
「老媽在你們那邊住的時候會不會鬧著要去銀行領錢?」母親透過通訊軟體傳了這樣的訊息給住在台中的小嬸。每逢過節,祖母總覺得要像三四十年前那般備辦雞鴨魚肉和糖果餅乾等供品,才不愧對神明祖宗,這點在我們這一輩年紀尚小時也許未有太多深刻的感受,只記得每年過年直到初十五,餐桌上依然滿溢除夕初一時祭拜的雞胸、鴨腿、筍絲湯等等。
過往農村社會的鄉人不得已粗茶淡飯度日,只有過節時才能品嘗鮮魚豬雞等祭祀供品,我父正值發育年紀時,肉也沒機會吃得幾塊,只因兄弟姐妹多,雞腿鴨胸這般肉質鮮美的部位亦由勞苦養家的祖父食盡。那樣的生活結構裡,小孩不可能擁有自己的零用錢購買正餐之外的點心,當時的甜食也不若現今中山站烘焙小店的馬卡龍那般精緻爽口。現今鄉下仍有許多人家過年祭祖會在神桌邊擺置紅色、白色糖衣的麻花,這種零嘴往往從菜市場一抓就是一大包,倒出來賣相品質良莠不齊,色素糖粉沾滿手指,孩童吃畢總捨不得那風味或歡快在味蕾消逝得太快,常見神桌上一供出麻花條,不出一炷香的時間便給頑童偷吃見底,趁大人未見前,便躲到後巷品舔手指上僅存的糖砂。
我們這一輩的生活景況固然不若父執輩那一代,但每年祭拜或大年夜上桌時,我們家族仍保留說吉祥話這樣的習俗,是以哪道料理帶著什麼典故或家族記憶,我們幾個晚輩就是說不詳細,也絕不陌生。然而隨著我們越長越大,越明瞭繁文縟節的祭祖與年夜飯支持的家族關係,竟是淡薄得讓人黯然。
我祖母,與其說是個窮怕了的農村女人,不如說她骨子裡承襲過往大家族持家的揮霍作態。她生於日治時代某一商賈人家,卻是偏房所生,無奈分家後隨意被送到陌生的鄉野做童養媳,從鄰人耆老與祖母本人口述,她至今無法接受那些薄情的欺侮與命運的作弄。
「你不覺得她看人的眼神總有股恨意。」十五年前,大伯同我父親表明,此生再也不踏進老家,遑論年節時分。祖母常奚落出身平常百姓家的大伯母,認為她不配做她的大媳婦。大伯與大伯母從小本生意,所賺所得全數交由祖母理財,幾個兒女亦安置老家由祖母照料,孰知祖母重男輕女,還因兩個堂姐神情眉宇近似大伯母神韻,而有虐待情事。當年我母親剛嫁進門,便曾目睹祖母耷拉小堂姐辮髮毒打。大伯與大伯母知曉此事,稍事追究幾句後,決定帶一干兒女出門踏青,散心之外,也是為了表達父母照顧失職的疼惜。祖母當時或許以為大伯賭氣或是氣急上心,竟哀嚎似地衝上屋頂,作勢跳樓。大伯與大伯母在老家門外跪膝一天一夜,不知祖母脾性的鄉人還以為夫妻倆不肖。兩人在祖母氣忿稍平後,決議舉家搬遷,在異地重新開始。
在那之後,由於大伯一家人常態性缺席,我們家族每逢過年總得聽祖母在年夜飯桌上以不堪入耳的詞彙毒討一切令她不順心的人事。一哭二鬧的情狀只能用雞飛狗跳形容,少有人真心期待除夕夜或大年初一上桌能與親戚餐敘閒聊過去一年來的見聞與辛勞。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怎麼就沒有人意識到祖母或許已經病了,甚至,她的病可能令我們全家族的關係陷入萬劫不復。
「別把這些事掛在心上,為這樣的事生氣無非在懲罰自己。」小嬸這麼與母親說。我與母親知曉小嬸這兩年來皈依佛教,餐餐全素,每晚打坐的結果竟也治好多年來的失眠與肩頸痠痛。過去小嬸攻讀博士班時,曾委請祖母到台中照顧還在上托育園的堂弟們。直到堂弟們上小學後,小嬸教職工作已逐漸上軌道,便決定親自照料小孩的功課,與祖母商談這件事時,祖母「喀」的一聲,霎然跪坐於地,對著小嬸嗑響頭。如此不明所以的行徑,令小嬸長年活在罪惡感與淺眠之中。
祖母與小嬸其實都是自小得不到父母疼愛的小孩。小嬸的父親性情嗜賭好女色,當年為了債務與女人,小嬸父親避居東部,令小嬸在台中港光腳向警員借錢,搭車前往高雄向旁系親戚求援。也不知是怎樣的執念,出社會後,小嬸四處打聽父親下落,得知她有一群同父異母的兄弟姊妹,她與他們保持似有若無的聯繫,直到她父親床榻病危——出乎我們全家族意料之外——她竟比誰都傾心照料,甚至打聽道觀為她父親供神求佛,藉以在西方世界覓得一安魂之地。
眼前那面黃肌瘦的老朽可能於她而言早就不是父親,又或者,她必須給自己一個交代,理解自身這些年來的勞苦與感情是托付在怎樣的期待與落空中,反反覆覆,終於成恨。她必須凝視眼前老人死逝的一切細瑣,方能埋葬原應嘆息的緣。
至於小叔,他本性是個好戰、好比較而情感淡漠的人。儘管過往由父兄長姊肩負家計,要他只管專心讀書,他卻也在假日從學校宿舍返家,幫忙家屋繕修或農作雜務等,未曾偷得半日閒,然而在兄姊眼中,他卻始終是那個生活相對寬裕而未曾為家庭吃過苦的么弟。是以,幾十年來,凡節日甚至祖母住院,小叔往往遲來。或許是解嚴時期以降,兄姊經商積累的財產遠多於擔任教職的他,在政黨輪替、經濟成長疲弱的那幾年,他投身製造業顧問工作,覓得良機且慎思布局,在十年內累積相當驚人的財富,也將一個兒子送往麻省理工學院深造,孰料卻未曾邀請兄姊等親屬到他獨門獨院的家屋作客。
——我小叔與小嬸兩人儘管成長過程都心懷不被理解的苦悶,兩人在結婚後卻因政治宗教議題與教養觀點相左而終於分房。這是我堂弟告訴我的,儘管父執輩們有諸多如死結般沒有答案的問題,我們堂兄弟之間互動卻很簡單,一直以來都是球類運動和電玩的最佳拍檔,或許男生與男生間幼時的感情要開展就是這麼容易,我們如今又在不同領域鑽研著,幾無利害關係可言,因此我們年節時分總相約在家裡鬧得雞犬不寧時,躲進房內遊樂,或是踅到廟口鄉野間感受不同於都市生活的閒散氣氛與美味小吃。
至於我父母,我很難想像他們對祖母抱持怎樣的感情與想法。距今約莫三十年前,我父母有了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大哥,不過也因為工作緣故,暫且託付給祖母照顧,雖然當時祖母不再需要下田農作,但是照料大伯的幾個大孩子和我那襁褓中的大哥可能仍分身乏術……大哥在出生半年後因腦膜炎延遲送醫而夭折。母親從未提過她的眼淚。在我中學時期,曾有連續幾年,父親都會領著我在中元節到嬰靈廟祭奉,有師父說,除非我婚娶,否則大哥將不投胎。然而我曾經問其他通靈友人,他們認為,歷經這幾多年,大哥不可能還落單陽世。我將這闡釋轉達父親,為的是消抹他心裡的沉重。
「你看客廳有一對音響,那是我父親給我的嫁妝。當年我進門,你奶奶對我叫囂,那樣不經用的東西擺在家裡也是徒然。」每年年夜飯的座位配置,晚輩理應敬陪末座,因此我的視線總能瞅見那副年久未用的音響。每年尾牙期間大掃除無論姊姊或我,總細緻擦拭那副音響,儘管能在那台機器上播放的唱盤都折舊了,我們仍抹去塵灰,給組件上油,好似那是什麼無價的古董。
幾年前的初一午後,祖母獨自前往志工友人家拜年,卻是到晚餐時間都還不見人影,後來就醫得的診斷是失智症,父親和小叔才從祖母房間的各個角落,包含衣櫃、天花板裡,發現成堆未拆的西藥、中藥和衛生紙捲,潮悶與霉臭,簡直就像是蔡明亮電影《洞》裡的意象那般,出口在哪裡?無人知曉、無處可逃。
父親與小叔總算連絡上大伯,三人協議,祖母每個月由三人輪流照顧十天。
失智症常見的症狀除了迷路與不理性的收集之外,最常見的便是識得的人越來越少、短期記憶也將日愈貧弱。我是全家族晚輩中唯一沒在嬰兒時期被祖母照顧過的,是以祖母最先忘記我的名字,我一點也不意外,甚至還鬆了一口氣。我如今人在哪個城市賃居、學的是什麼專業,祖母似乎也不再在意,她只當我還是個中學生,見到我也只管要我認真讀書,少看電視等。這些年來,有祖母在的客廳,我們的家庭生活便安靜得只剩台語新聞播送或肥皂劇對白,期間祖母會倏地跳出來成為主角,演活過往年歲裡的家族創口,令我們的情緒沒有窗口。有時候鋼杯裡的白開水會濺得到處都是,餅乾屑會落在吸塵器伸不進的牆角,沙發座椅上會有淚痕與尿漬。
祖母住滿十天後,便由大伯遠道驅車載往嘉義接手照顧,父親迅即動手清洗沙發椅墊、浴室防滑墊、臥房腳墊,漂白水配方一比一百,沖洗再三,陽台晾曬,有時雨季一到,連日大雨、日照稀落,從大廈住宅落地窗看向遠方公路彼端,好似還能聽見祖母對著其他親屬挑撥離間的言談,他很好你為什麼不可以,你很好他卻還可以……
「十天怎麼過那麼慢?」大伯母過著半退休生活,有時候透過通訊軟體抱怨,總讓父母在手機彼端忖度她與大伯夫妻倆的真意。機構照護是父親與他兄弟們近來討論的主軸,然而乖僻的祖母曾在小叔家中不合理地使喚並毆打外籍看護,料想養護院所人員在照料困難的折騰下難免會有不盡人意的處置……
有時我聽祖母說話,她只管口無遮攔訴說一切,或許於她而言我只是似曾相識的面孔吧。據她表述,大伯只管伺候她吃喝拉撒睡,母子相看只會點燃謾罵、咆哮與後續更嚴重的冷戰。可大伯那方好似每回侍應用餐總得三催四請,每餐飯後超過十種的藥物更彰顯祖母將病氣作為籌碼的內在矛盾,這使得大伯在那十天內難以安排任何會議與參訪。
更有甚者,祖母每輪居到小叔家總不見小嬸人影,生活範圍也限制在房間、浴廁與飯廳。一經詢問才明瞭,原來小嬸在那期間都移住任教大學的教職員宿舍,堂弟們也不願在那十天返家過夜。小叔目前的工作模式偏向舒活族,家庭辦公室輔以智慧型裝置遠端操作,工作時間地點極為自由,一時半晌竟也兼有生活品質,又能全日隨侍。
今年A型流感大流行,我們一家四口相繼中標發燒,宥於祖母久咳以來免疫功能較差,我們決定頭一次不在除夕當天返回老家過年,孰料大年初四大夥初癒回鄉,老家門戶深鎖,神祖供桌不見任何發糕甜粿,同鄰居探聽,小叔竟四處叮囑:「切勿讓我老母親知道今天除夕。」
這是一個家族的結束嗎?抑或是各人小家庭必得面對的轉捩點?父親曾給我看祖父的一張照片,儘管照片泛黃,卻能瞅見那圖幀被拼組黏貼的膠帶痕。祖父過世那年,父親才上高中,黯然神傷整理遺物的過程中,原應哀悼嘆惋,祖母卻將祖父照片衣物等等剪碎丟往前庭水溝。父親說大伯嚎叫著跳進溝壑拾掇。
那真正是有病的吧?我只能這樣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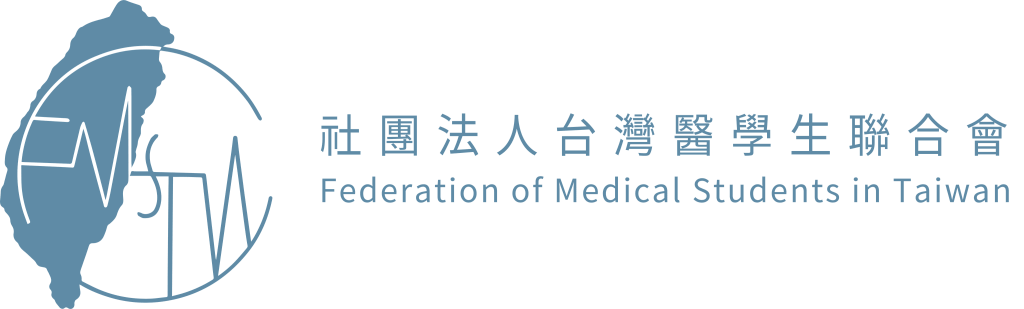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