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散文組佳作]陽明醫學五-林佳亨《南國假期》
「他是有執照的醫師嗎?妳覺得他夠專業嗎?妳怎麼可以這樣對我!」我看見她脖子青筋張狂下潛藏的憂懼,「我都已經生病了!還要當他的白老鼠……我怎麼這麼倒楣!」她蓬亂的頭髮和底色不均的淡妝概括訴說了病痛本身的故事性。
「我們醫生已經打過好幾個啦!妳看,他都已經打進去了——快好啦、快好
啦……再忍耐一下!」注射間的資深護理師不停安撫。
「好了。這是軟針,等會兒雙手可以自然下垂,等電腦斷層室叫號碼,輪到你了就可以進去檢查……」她提起粉紫色的小型女用托特包,眼眶含著淚似地轉身離去。我連她的臉龐都沒能看清,遑論知悉她來注射間安放靜脈留置針的理由。
「剛剛你那個角度沒抓好,幸虧你知道我在跟你暗示先拉出來一點點再往右邊那個方向扎。」資深護理師以鼓勵的眼神和提醒的語氣讓我能立即整理情緒面對下一位上前的年長榮民。
「我看你剛剛連拿針都不會哩!我告訴你,我眼睛好得很,你是不是真會打這針,我一看就知道!」他語畢後留下一段空白,似是等待我口頭回報以十萬分的信心寬慰他那隱沒於滑皺皮膚下靜脈內鼓動的老之可怖。
「你笑什麼!還不快給我打!」我以為微笑能緩和他高張的情緒,孰料招致意想不到的反效果,我也只得加快動作。
那天中午在員工餐廳吃的是冷掉的酢醬麵和鋁箔包裝的豆奶,儘管那絕對算不上極致美味,卻還是以一種流利的姿態倏地滑入不怎麼喊餓的胃腸,予人最低限度的飽足感面對午後一切繁瑣。我將餐具放上碗盤輸送帶時順道看向員工餐廳玻璃外的灰翳雨景,不禁懷念起家鄉新營的無垠青空,還有我的家人。
抱著這樣幽闇的心緒在臉上掛著微笑一連在科部裡飄來盪去了數天,總算迎來不多得的二天連假。無論車站人潮多麼壅塞、不管車廂乘客多麼擁擠,只要拿出在外科實習上大刀的肌力,我必能頂回南國。
真正踏進家門並且盥洗完畢時已屆晚上十一時。我走向廚房,看見母親從蒸騰的水氣裡撈出一顆又一顆斗大的手工水餃。韭菜是母親那位從台北嫁來新營做田園媳婦的好友所贈送,內餡的蝦子則委由銀行上班的表嫂央人從漁市裡帶來最肥美的,至於水餃皮和絞肉是從傳統市場裡向熟識的攤商掂斤秤兩而得——或許由於經商營賈的父母原出身純樸農家,那時代沒有無下箸處的山珍海味,卻有的是新鮮的雞豬青菜在年節時分飽暖一家子,因此母親家中掌廚首重食材品質,為的是讓我們餐餐感受到圍桌吃飯的凝集與溫情。
用木筷將水餃挾到灑著些許蔥花的日式醬油碟裡沾裹後再放入嘴裡,那鮮甜肉汁的熱燙是如何刺激舌苔上的味蕾自是不在話下,更重要的是,一股家庭生活的豐足感填補了拌食那碗酢醬冷麵時相隨的呆滯與空虛。
父親或許發現我眼角濕潤,便偕同母親拉了木製家具的椅子到餐桌邊與我閒聊街坊鄰居的近況。鑰匙印章店的阿姨從北港後頭厝兜了一圈回來後送來一盒解饞的綠豆椪餡餅;住在台糖五百戶獨棟透天社區的蔡老師夫妻隔幾天後要嫁女兒;性情乖僻的堂伯前陣子高齡仙逝,孰料孫執輩與老同鄉竟無一前往致意,這件事令與堂伯年紀相仿的祖母慨嘆不已……
說起來生活終究是這些日常瑣事的拼接吧。我邊聽邊從冰箱的冷凍庫裡拿出父親預先榨好、冷凍的檸檬原汁冰塊,放在馬克杯裡再倒入適量的溫開水以資解膩。我平常也會在醫院鄰近的市場買幾顆檸檬在宿舍裡製作完全不加糖或蜂蜜的檸檬水,在晚飯後配著水果吃將掉。雖然沒經過科學考證,但我認為那有助於舒緩工作一整天和傍晚慢跑、重訓後的肌肉痠痛。大多數朋友總覺得那樣比例製作的檸檬水過於酸澀而難以入口,我也只苦笑回應那是從家裡帶著北上的飲食習慣。
除了水餃和檸檬水之外,我這次回家亦相當期待母親烹煮宜蘭那位愛釣魚的二舅在今年春節送我們的兩尾大土魠魚,還記得是放在保麗龍箱裡請宅急便用冷凍貨櫃車快遞送來。父親在磨刀石上磨光幾把菜刀後,母親便熟練地包辦去鱗、挑骨、分切和裝袋等差工,每一袋的魚肉分量足以成為三至四人小家庭晚餐桌上讓人食指大動的菜餚。大街小巷較常見到的土魠魚菜餚往往是先將魚塊在油鍋裡先行炸酥表皮至金黃色,再加入羹湯、滴點烏醋,名為土魠魚羹;然而居處家常灶腳的主婦也慣習在炒鍋上摻點蒜簡單煎過,讓土魠魚自身的油汁滴落在白飯上配著吃更能凸顯魚質鮮美和嘉南平原白米的 Q 軟。大伯母和小嬸都說母親是調製糖醋醬
汁的高手,眼見她將醬油、糖、白醋和蔥蒜爆香後再和著魚肉雜炒悶上幾刻,就能在年節時分妥貼全家族成員的脾胃。凡糖醋土魠魚一出,白飯不知又要配上幾碗。
連假第一天午後吃畢這道菜餚後,某位曾在父親店裡工作過幾年而後因婚隨夫喬遷而離職的女職員從學甲家鄉帶來一大袋顆顆宛若高爾夫球般大小的虱目魚丸,過去曾有幾回請託國中同學的家人代買過學甲鄉的虱目魚丸,那味道之鮮美就連我那受日本教育、家族裡出了名挑嘴的海產通外祖父也讚不絕口。當下父親便決定晚餐時他要親自進廚房以那些虱目魚丸搭配冰箱現有食材煮一鍋陽春麵。
儘管名為陽春麵,我們家特製的陽春麵可和源於江蘇、上海的那種方便的白湯麵條八竿子打不著。父親的陽春麵基本上會先在滾水裡置以大量高麗菜、少許番茄熬製清甜的湯底,再備好海中雞魚肉罐頭給湯汁加一帖魚肉甘味,接著添放魚丸、水煮蝦等,待其一併熟透後即下寬白麵條和蔥末提味。有時我還會在旁邊煎幾顆半生不熟的荷包蛋,或驅車前往區公所附近外帶大份的臭豆腐,那攤販不會將豆腐炸得過酥,好讓豆腐能充分同特製醬汁、蒜泥、辣豆瓣和台式泡菜混合,在味蕾上印記口頰難忘的味覺記憶。
眼下這些對於懷舊菜餚的敘述都是我十八歲離開新營前就建立起的生活印象。一天天很長,一年年卻很短。大學期間有時回新營看見熟悉的店家搬遷或母校改建,才學會對記憶的真實性存疑,不過也唯有在家鄉上街逡巡感受那人情與街角巷弄的地理盤繞才覺得自己在醫院飄忽的日子有所依歸。
隔天我起了個大早,獨自上位處交通台附近的傳統市場尋早飯吃。首先我在市仔口一家虱目魚肚粥店前坐下,叫了一碗無刺魚肚粥,還請熟識的老闆娘為我加幾顆新鮮的蚵仔。那粥飯在魚骨高湯裡要煮得爛需要一會兒時間,我便同老闆娘的女兒即刻舀了個蒸虱目魚頭和鹹瓜來剔牙。關於魚頭有段故事:在物資匱乏的年代,有位母親都將魚肚和魚頰邊肉給小孩分食,小孩見母親都啃魚頭配飯,以為母親愛魚頭不愛魚肉,長大後幾個兄弟同老母親吃飯竟特地將魚頭分將出來挾到老母親飯碗裡……這段口傳勸世故事杳無後續,任憑聽者在那魚頭的舌尖餘味中細品何謂遠近高低各不同。
罷了,老母親可能如是想。
罷了,誰開懷誰忿懣、誰順心誰怨懟,終究只能付諸時間裁判消解,莫與自身過不去,且在當下做個豬頭,等會兒沾著蒜頭醬油吃完這碗虱目魚肚粥就踅去吃豬頭飯吧!轉念、轉念,當作是修練。在外科曾受某位老師如此教誨。且看那豬頭在滾水裡熬啊熬,終於同不易吸水的在來米在鍋裡炊得乾鬆香軟、彈牙可口。高中三年時不時在晨間食豬頭飯配香腸、酸筍絲和白菜滷飽餐,卻沒看透那白黃米粒間的尚善哲思。
腆著肚皮走進家門才看見父親與母親在玻璃圓桌相對而坐,啜飲濾掛式曼特寧咖啡。父親與母親相敬如賓、琴瑟和鳴,今年夏天婚姻屆滿三十年,我想就請在天母拜藝的書畫老師給他們刻一對饒富古風的金文石印以茲紀念。若非他們一路走來為不懂事的我周全食衣生計等基本需要,我何德何能追趕所想所愛直至如今光景?父親與母親這些年來是否覺得我成熟了?未來若有那麼一天我在職涯中稱心了,他們是否依舊精神如是?
繞了一大圈,原來生活祇是平凡最重要。
「難得回來一趟,今天吃完午飯去鹽水大眾廟參拜吧。」父親見著我便咧嘴提議。鹽水大眾廟源遠流長,可追溯至明代永曆年間,鄭成功部將何積善於八掌溪、急水溪匯聚的月津碼頭興建聚波亭以慰勞商旅路途艱辛;直至乾隆年間,信眾為感念雷府大將軍庇佑行船無恙,便在聚波亭古榕樹邊建了座大眾廟以供神尊。一府二鹿三艋舺四月港,可惜滄海桑田,昔日河港竟成溝渠,好在每逢元宵鹽水蜂炮最是熱鬧的王船炮城年年仍鬧熱不斷,旺香火也光采那鹽水古城。
從新營到鹽水大眾廟並不遠,沿第一傳統市場所在的復興路開車直通到最底,轉進信義路即為鹽水區,順著中山路驅車,看見八角樓後拐入中正路,若瞥見圳溝,探尋一下聚波亭舊址,那大眾廟就在對面。
撚燃二十支香後,首先拜過天公,再進到正殿瞻仰主祀雷萬春將軍那鬍鬚似是年年增長的神像,我在心裡默祈家業昌隆、身心安康,料想百幾年來,善男信女等必也心懷悲怨抑或憂喜交織地前來祈求天人無災,家宅無厄。人事人心原是橫亙古今皆同,這點雷府千歲爺就是了然,也只是安泰地俯瞰持香的我們。
雷千歲左右各是范將軍與謝將軍,三拜過後父親與我便繞至後殿敬祀地藏王菩薩。「安忍不動,猶如大地;靜慮深密,猶如秘藏。」地藏菩薩化無量身至無量地獄,本願在救度眾生。
「地藏王菩薩又叫幽冥教主,管理陰間。你看過生死交關——好好地拜一下,地藏菩薩會保佑你。」父親叮囑後,我才知曉父親那柔軟的疼惜。午後春日穿過樹梢灑在地藏菩薩金爐邊婆娑躍動,我的心緒此刻始真正清快,我抬頭仰望迥異於黯沉臺北的青空南天,寶貝地細數眼界所及每一片雲白,我想這就是我不計時間長短也要乘車南歸再見的風景,父親、母親及我鍾愛的飲食、人情俱在此地變亦未變地停佇。這大眾廟同祀了這麼多其他神尊比如觀世音菩薩、張巡元帥、福德正神、註生娘娘、文武財神、文昌帝君、月下老人、太上老君等,莫不是代表過去每位行經月港、居所不定的旅人們共同心繫指望的人生道標?往後日子我亦同旅人般將持續不斷結識新人、料理人事,然而無論再怎樣殫精委屈,我都會想起母親以料理疼惜我、父親以廟神祝願我的這段南國假期。
我以平和感激的心緒將香炷插上金爐。儘管這會兒我將再度離家遠遊,但我已能挺起胸膛面對未來一切不安與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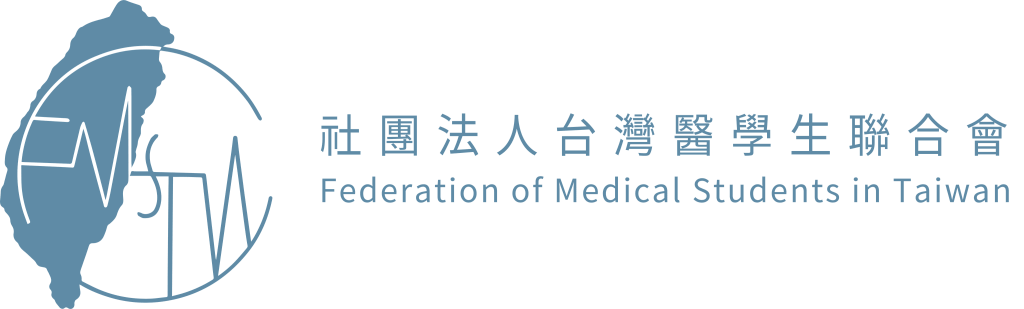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