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散文組佳作]北醫醫學六-尹睿慈《非典型》
外科見習的日子邁入第六週,這週跟的主治醫師張醫師,是個天才。
張醫師的年紀三十六,在主治醫師中算是年輕的。他的眼睛是雙聰明的眼睛,頭髮和鬍子不修邊幅,十根手指頭纖細修長,身材挺拔,走起路來白袍會飛,袍子的右手袖有褪色的血漬一滴。每天固定查房兩次,沒有意外的話是早上八點和下午四點,步伐快、雙手交叉握於背後,對待病人不卑不亢,「謝謝,謝謝,謝謝張醫師…」常在每個早晨此起彼落,他也只是淺淺的點個頭。他的記憶力非常驚人,一天記住我的名字,一個月記住所有見習醫學生的名字,一年前只跟過他一周的實習醫師一年過後他仍能夠指著人叫出名字,更別說每個病人的床號、長相、名字、情況、兒女甚至看護,絕對是一清二楚。開刀房裡他只會露出一雙眼睛和一付眼鏡,他的刀房專屬拖鞋髒到不行,曾經是白色的地方全被消毒優碘和斑斑血跡覆蓋。他開刀時性子急但脾氣不差,常和護士們閒聊,偶而也講講黃色笑話,他的刀法快且流暢,縫針、綁線如行雲流水,眨眼間已連續打好三個節,剪刀剪下那刻會熱血的大喊一聲:FIRE!驚嚇全刀房的人。他對開刀充滿熱情,每個月平均開一百台以上。是我刻板印象中也是想像中的完美外科醫師。
一次原本預定的腹腔鏡手術,因為病人腸子太過腫脹得行傳統開腹手術。 「來!大燈開!我們改open!」張醫師一聲令下,隨後快速移動到病人對側。在我看來,他連走路把拖鞋拖得很大聲都令我覺得帥氣。
「幹」字常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眾多人的語助詞,他說過:「幹!搞什麼東西!」、「幹!內科說沒有他們的問題?」……。一天刀房護士們開著玩笑話: 「…… ,張醫師都偏心,他都只打兒子不打女兒的……。」
「幹!阿我兒子就很白目啊!」
他只露出兩隻眼睛和一付眼鏡,頭也不抬地繼續開刀,沒有人看得出來他的表情。我們也只露出一雙眼睛,卻也不敢像護士們一樣放肆地笑著,生怕一個不小心吵醒了麻醉中的病人一般。
每個星期四早上和星期五下午是張醫師的固定門診時段。他的病人數不少,以術後追蹤居多,卻不同於我之前跟過的任何門診教學。
「張醫師,加油!」一位來做癌症術後追蹤的女士走進診間,雙手握住張醫師擺在桌上的那隻手。
「怎麼這麼說?」
「我在醫訊上看到你,你好棒,現在擁有自己的專屬團隊了要更加油,你不只救了我,還要救更多的人喔!還有,你上面的那張照片好帥!」
「謝謝你,我會的。最近還好嗎?」
「對了,這個送給你,希望對你有幫助。」病人從包包裡拿出一張關於癌症手術的剪報。
「這前幾天的聯合報我好像有看過,謝謝你。」張醫師小心地把剪報收進抽屜。
隨後病人神采奕奕地走出診間,淡淡著妝粉味還殘留著。
另一位病人是這樣的,四十五歲男性。
「嗨!張醫師,你好嗎?你的鬍子今天有點亂。」
「唉呀,最近比較忙沒時間刮鬍子。」
「沒關係啦!你還是一樣,我也是。我這次很好,都沒有什麼不舒服,那下次約什麼時後回診?」
「很好阿,那幫你約三個月後好不好?」
「之前每次都是一個月回診一次這次為什麼變三個月?」
我看了看電腦螢幕,過去並沒有任何重大的過去病史,讓張醫師開過一次急性盲腸炎手術,但那也是兩年前的事了,更疑惑他兩年來每個月固定回診追蹤什麼?也許並不是疾病,是張醫師。一整個上午,面對病人千奇百怪的問題,張醫師都能見招拆招一一化解,他沒有回過頭來看我一眼,除了看見桌上越積越多的謝禮外,卻也明白了病人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
一天,我按教研部規定撥電話向張醫師確認教學時間。
「老師,請問你今天下午有空幫我們上課嗎?」
「喔,你們想上課嗎?」
「嗯,看老師您方便呀!」
「欸可是我還沒有想到下午要不要上課。」
「那…老師您再考慮一下沒關係。」
「誰叫你打電話給我的阿?下次不要再打給我了!」他說完斷然地掛了電話,我看著話筒傻愣了兩秒鐘,但語氣聽起來並沒有很震怒。
這個下午一如往常跟著張醫師查房,查完七樓病房後上九樓和十一樓看外科照會病人,結束時我們走下樓梯。
「沒事了耶!不如我們來上課吧!」張醫師回過頭來說。
同學和我驚訝的互望。這時我們心裡想的絕對一樣:「什…….麼!」也許連那個「麼」都還沒出來,張醫師再度轉過頭來。
「怎麼樣?不想上課是不是?不想上就不要上沒關係啊!」
我們完全來不及反應。不是哪!是沒有通知到其他同學哪!也許連那個「不」都還沒出來,張醫師的下一句話已經出口。
「兩個人上可以吧?人數應該不重要吧,想聽的就來聽聽。」他的反應永遠比我們快上一拍,以上的經過約莫發生在一分鐘以內,而我們已經不知不覺下到了七樓。
關於上課的情形和內容我說不清楚,因為我們完全抓不到重點,他的思緒太快、太跳躍、太無邊無際、太天馬行空,對於我的們來說。課堂結束他總會以「有沒有問題?」做結,外加一句「不限於任何主題」,但得到的答案不是「這問題沒什麼好問的。」(問題:老師開刀為什麼要大喊FIRE?) 就是「這問題很好,Sabiston一本才一千多頁,回去自己看一看。」(其他學術相關問題) 他回答問題的口氣不囂張也不嘲弄,就如同向病人宣布腫瘤是惡性的一般,不帶表情。
而他問的問題有千百種,但最後一句話總是「回去想一想,這書上不會寫,網路上也查不到」,沮喪的是永遠也得不到他親自解答。就這樣,他沒有想要對我們施招,卻時時刻刻都不知不覺地放出暗箭,而我們一招也接不住、猜不透,眼看著我對外科的憧憬即將被徹底擊碎,直到最後一天查房。我們走在寬敞的迴廊上,可以明顯聽出前後的三雙腳步聲和回音,走在張醫師身後,他飄揚的長袍彷彿一面連身鏡,映著眼前未知的路,並且顯得格外無止境。傍晚的夕暉從十一樓的落地窗灑進來,張醫師望向窗外深吸了一口氣後悠悠地說:「你們對外科有興趣嗎?很多人說現在台灣的醫療環境差,外科的給付低、風險又高;我說真正有興趣的人一點也不害怕這些。你們要想想自己想成為怎樣的人?我不需要對你們多說什麼,我只是表現得讓你們想成為這樣的人。」
沒錯,他從來不會說他做了些什麼,不論對於病人或學生,而病人的情況一天天好轉,在洶湧的汪洋中尚不知懷抱著什麼使命載浮載沉著的我們,卻也依稀看見了遠方的燈塔在閃爍。一週下來我想我們終究是凡人一個,又或許是雙未成熟翅膀,想飛翔又怕受傷。但他那股發自內心喜愛開刀不為什麼的熱情,是我唯一能夠學到並且理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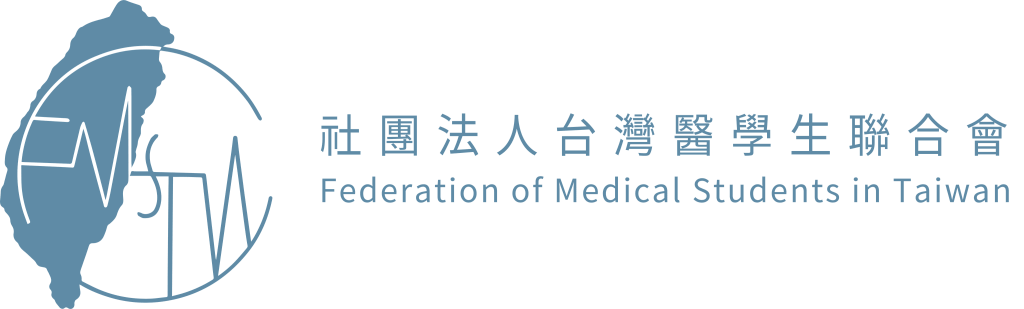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