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散文組評審獎]吾名氏《我們曾經聽見的看見的》
一直到你不再回信跟我討論虛無的那一天,G,我才感到整的生活是多麼空虛,空虛的徹徹底底。
有好一陣子,我不願在那一站下車,捷運總是走走停停,卻依舊會到終點;那些看著捷運一班班駛過的情景,我想,是不在有了。有人說要把生活哼成歌,有人編織錦繡衣裳,但如果要寫成一部和聲學,泛音不一定有,更多的是我們的想像。夜雨聞鈴腸斷聲,但四方寂寥無響更揪心。分開後我們跌跌撞撞,聽音辨位般摸索對應的波頻,在小調或減七和弦中安身。路上有許多傳說,位置和口型如鬼火般在轉角螢螢綽綽,一聲和絃便將飽滿的情緒刷出一個大洞,而有水流乎其間,常相左右錚錚在生活的隙覷裡。
(對光影的迷戀,也許是某部電影片尾,主角在長長的馬路上越走越遠,彩度逐漸下降時,他所驚覺的一種
無可挽回。)
(「每次看到舊相片總是泛黃…感覺三十年前的人,看出去的光景應該都要有點昏黃…」就像六十年前應該是黑白的一樣嗎?他無法想像黑白的植物園應該長什麼樣子,像底片?他記得小時候喜歡收集底片盒子,似乎可以做成空氣槍之類的東西;而曝光過後的膠卷,白首烏面的同學露出黑黑的牙,色彩被翻轉,顛倒世界。所以荷花該是灰灰的、朦朦朧朧,蘇鐵是否像剪影一樣沉思。他不由得想到卓別林《摩登時代》,不是因為劇情,而是黑白片的緣故;齒輪看起來更沒有生氣,作業員成了簽字筆塗鴉的動畫。父親可能跟他說:當年我們在美國念大學的時候…於是他急忙找出當年相簿,扉頁泛黃,相片當然也泛黃,大白天卻像黃昏,暮氣在一個個定格的時空中爬行。)
G,一直以來,我以為文藝復興會是我最後的皈依,我以為只有經文歌才能毫無阻礙地走進我們心底。自從古典音樂版權解禁,大量的譜開始在網路上流竄,滑鼠點開,宛如金色流沙傾洩而出。舊時的繁花盛景原是如此建構,我們將譜剪成長條狀,將其扭成麻花,試圖觸摸音層之間疏直的紋理,就像幾個世紀前岩石的風化刻痕,俐落卻綿密地,將我們充滿。
又或者,喜歡某種風格的音樂,只是為著異端的誘惑?我們是否曾著迷於新世界音樂,不和諧音程是迴轉的光年;如同試圖理解巴洛克大鍵琴一閃即逝的聲響下、是否有中世紀的精魂?也許強迫自己看華格納的歌劇,尼貝龍的指環傳說隱隱與紐倫堡的歌手抗衡;不談《魔笛》而追求《瑭璜》,帶抹標新立異的性格甚至不聽流行歌,噢,有聽,但是只聽某一段時期,介於校園民歌和目前檯面上當紅小生女旦間的模糊地帶。
(樹葉枯萎會變黃,那是將來的事;可是過去也會變黃,是什麼追趕著呢。他小時候感冒,母親帶他去診所看病,他總是盯著牆上的證書,多久以前掛號櫃台後的醫師就坐在那裏了呢?許多年後他身高抽長,擠在一群亂跑亂跳的孩童之間顯得侷促,每年的流行性感冒標示著一個循環,牆上的米奇米妮也跟著發白,變成卸了一半妝的褐老鼠。好像它們也被曬黑,衣服也因洗太久而褪色。)
(離開高中後許久,他都沒有再進去過。也許說不上是近鄉情怯,但是一想到記憶中的建築可能不復以往,腳步又踅了回來。最近一次同學會,無意識地跟著大家穿過校園,恍神在排球場上。過一會兒有某男子數人邀約挑戰,忽然五六年前的畫面從稀薄的記憶破冰而出,他記得陽光直射的午後,所有人都成了剪影,無風無雨,空氣凝結沒有聲息,躍起扣球都成了快門貼圖,像是連續動作圖片在播放。當年他們都還稱得上身手矯健,土黃色的卡其褲捲到膝蓋的高度,台北在沙塵暴,天空泥泥黃黃,幾個人像就開始失焦,失焦在只有球聲的操場。)
(他的記憶也開始失焦。)
G,記得你很喜歡講德文,而我至今仍未領略其文法奧妙。那些齒舌輕擦的瞬間,氣息在口縫的噴吐,是不是有略為刺耳堅定或憂傷,徘徊在夜曲後方不散;也許字音是情緒的延伸,連串的子音就成了交織的揣想。是這樣嗎?所以遺落在我們後方酥酥碎碎的耳語,也是晦澀不明的線索?
曾在電視節目中,聽到蒙古牧人示範呼麥,無字無詞,而整片草原為之唱和。大漠孤煙的民族,只有在撐滿天地的泛音間才能再現。如果閉上眼睛,那聲音便恍如從遙遠的時空穿來,夾帶駿馬的嘶鳴和風沙的呼號,使所有文字體都粉碎隨風而逝。想起那些年我們的通信,電子郵件的往返,終究隨著信箱中毒或是論壇被色情網站入侵而不剩殘骸,內容也隨著時間的風沙而在海馬迴中日漸稀薄,終至成齏。
之後在某個機緣下,聽到一首越南流行歌;詞意大致凡俗,諸如你遠去前我不懂得珍惜,你遠去後我心悲傷之類。但是在東南亞特殊的聲調發音下,纏綿的單相思旖旎蜿蜒,盤伏在港邊、機場分離的渡口,渡口相送的情人,情人的心口上。那一刻開口欲道別都泣不成聲,唯有音樂能代替我們傳達隻字片語。
(他的記憶也開始失焦。
回想關於操場的記憶。關於戶外的記憶。關於教室外的記憶。
他驚覺,所有的畫面似乎都被過度曝光,陽光過於旺盛地發散在磁磚、植披、空氣中;連畢業典禮當天下午,成千張木椅魔術般從草皮上長出來的偉大時刻,都彷彿過熱而融化,流淌成交雜咖啡綠的痕跡。再往前推,再往前推,齒輪逆行要趕在太陽的金光到達之前。國中時去的東眼山應該就是青翠長綠吧?怎知卻霧濛濛(敢情是當天飄著細雨),甚至不確定樹葉的形狀是不是自己所想像出來的;國小躲避球賽,他記得球的速度讓他總是害怕地閃躲,一群小學生推推擠擠,場外一位壯壯的男孩用足力氣將球扔出——整個動作卻突然被調慢,他清楚看到手掌上肌肉如何一吋吋緊繃,指尖因壓力而泛白,黃色的球卻變的無限巨大,大到他再也看不清比賽的結果。)
我沒有跟你說的是,後來爵士闖進我的生活,低音大提琴不斷在腦海內彈撥,長號一聲把城市帷幕裂成兩半,雨點打在傘頂如琴鍵,高音即興清脆琉璃。很多年以來我都不聽爵士樂,甚至有意地避開,每每覺得藍調太消極、銅管又過於喧囂,咖啡館的背景音樂已經是容忍的極限。但是也許是不經意,拉丁爵士伴隨手鼓鑽入耳膜,在各個樂手交相表現時,爵士闖進我的生活。
文字按照規則排列,助動詞名詞形容詞各有其位。喬姆斯基提出語法天生,G,所以你的話語是依附在早已建立的複雜結構上,有固定的生長方向。音樂卻不是如此,尤其爵士不是如此。
什麼是風格什麼是定律,我就是風格我就是定律。把五線譜重新對折,剪出一朵朵紅花,讓它隨風飄灑。如果有一天我們都得了失語症,句子破碎、文法猖狂;如果有一天書寫的世界毀壞,程式語言主導城市的節奏,至少我們還能發出高高低低的哼鳴,讓生活的轉折和起伏化為甜美或悲傷的希冀。
(多年後,他試圖利用口述歷史的方式,重建一條未被文字記錄的光陰長河。在文字稿的整理過程中,他腦海不自覺浮現出這些受訪者年輕時的場景:平頭嘻笑的少男,在他所搭建的舞台翻滾青春。可是怎麼也擺脫不了的是那抹暈黃,如影隨形直要染上每一張臉,換成颳風、晴天,眾男鼻息噴吐隱隱,聲音裡有了時間的痕跡。)
G,也許在一個以光速向前直進的社會中,我們回頭栽進的,是鮮少被提及的石窟,遺跡隱隱漫漶在風中,手上擎著火把,照亮一點點褪色的壁畫。你常常想勾勒那些最美的最真的已然失去的,相信時光的藩籬可以被消融,只要我們願意,便能前進過去、回到未來;而我卻以為,聲音和光影,左右著我們的意志,無論如何,我們都將是二十一世紀的波希米亞人,流浪之餘,過去的巷弄卻在沒有警覺的轉身瞬間,早已扭曲變形。
如果能夠將記憶的世界凍結,讓我們用最快的速度回頭奔跑,將會看到許多幅巨大的切片;但是從細節開始,已經長出失真的苔痕。多年前我獨自到北海岸,風中鹹鹹的浪聲告訴我太平洋就在那裡;可是海逃依舊翻騰吐息,眼前的海卻不是兒時瞳孔望出去的,藍。
正如我們之間曾經發生的,早已消失殆盡;儘管在某些暗暝的時刻,我們都很努力、很徒然地招魂。
評審評論
鍾:我很難抗拒感情很濃烈的作品,但我覺得這篇有點小失誤是結構人稱有點亂,你我他,人稱很多,很奇怪,不過有些東西拼拼貼貼就有很微妙的感覺。作者心裡感覺有很多東西未完成,恰好是讓我感到魅力的所在,想要跟蹤著他,究竟他會走到哪裡。
柯:雖然看不懂,但是還是有一種力量,作者強而有力的支配,雖然我不知道他要幹嘛,但是卻有一種力量壓著我想要把他讀完,那些你我他的看不懂其實我也已經放棄了。有幾段我覺得我自己寫不出來,需要年輕人對世界充滿情感、充滿感覺,所有的東西都對你別有意涵,要是青春的狀態才有辦法寫出來的。我特別喜歡的是他寫聲音的部分,因為聲音其實是很難寫的,他以音樂跟語言串整個文章,但他沒有刻意著痕跡的去做這件事情,是為了要帶出某種情感,而情感即使我摸不透,但看起來感覺還是很舒服。特別是最後一頁中間的部分寫得很好,是一部很有才情的作品。
評選結果
編/李/柯/鍾/計/名
15/03/05/04/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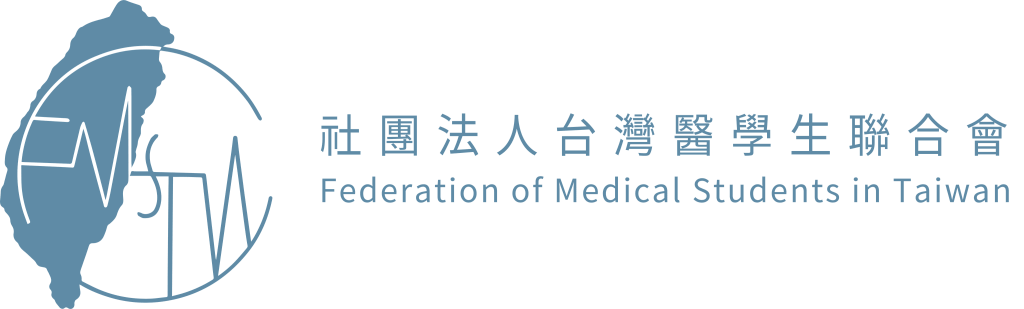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