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之後的他,現在與那一棟樓屋同等地蒼老了。在年年顫寒的季風底,他目睹二樓陽台邊界上,那排鐵欄杆逐漸腐蝕脆化,一冬薄似一冬,突然於某個他不在場的瞬間,崩碎瓦解。黯赭色的金屬骸片散落地面,粉繡紛然,缺了一大口的橫欄,虎虎正對著神明廳內觀音佛祖的眼眸。
那是濱畔,是海平面之上一切以異常迅疾的步伐消亡的鹽鹼地域。十年前一場哀傷緩慢的強震,使得門樑外側的一大塊壁面,脫離原本位置墜毀,露出內裡嚴重鏽蝕的鋼筋,他彷彿覺得自己的最末一絲抵抗意志也同時自身體摔落。最末一次替欄杆上漆是何時?他己然記憶不起。但他知道,是要讓鮮紅的油漆褪為瘀血色澤的時間,更久,更遠之前的故事。
海風微微,像有太多太多故事要說,只要求一名無比耐心的聽眾。他知道母親是善於等待的,無騖無驚,肅然端坐,讓時間支吾著證詞,靜待所有埋下的線索終究水落石出。但他只覺得這是一場冗長且多餘的上訴,他只想帶母親離開荒謬法場。
多年以來,他反覆夢見自己開著車,依循反覆離開的那一條途徑,跨過大門,空盪廟埕,經過數不清磚厝矮牆垣,沿著新鮮亮閃,指向無際的柏油公路,回到繁華都市。夢境中一切難與現實辨別,並且他也感到一種疼痛在胸臆,突刺,恍惚。坐在身側的妻,看著窗外奔流風景,不屬於這年代的復古的大波浪捲髮在獵獵轉旋,風聲唬唬。他看見,妻回過頭來,竟然是母親,和妻一樣的年歲,顴頰斑點隱現,額上皺紋方要成形,安祥地對著他微笑。
工
透早透早,他悠然轉醒,手肘橫斜撐起上半身,視野被湧入窗子的天光填滿,又濕又冷的青灰色。那色澤有一種淡漠的熟悉,像飄忽遠近的凝視,好像母親瞳孔周圍的昏翳。他曾經壓抑著畏懼,靠近覷瞰母親那靈魂的窗口,但只見一片黑洞,只見母親眼瞼眨動,輕輕開啟,久久閉闔。
身旁的妻猶自酣睡,他輕輕撥了撥妻的瀏海,攏向一側,停駐稍息,小心翼翼跨過拱成小山樣的被窩,挾起床沿厚呢黑外套,踏藍白拖走出房間,啪搭啪搭過短廊入神明廳。神明廳門楣釘著五彩垂珠簾,一陣窸窣搖晃,龍鳳呈祥的圖案漣漪幻變,中央紅豔的囍字碎開來,又緩慢復歸,也像迷離的夢境未醒。他使勁推開廳內大片木框窗玻璃和鋁紗門,抬腿跨出膝蓋高的門檻,走上陽台,視野豁然開闊,廟埕在晨霧中寂寞,幾株欖仁樹粗枝大葉地在廟埕邊界倚牆生長,葉色已轉黯紅枯索,餘燼一般悶悶地燎燒,圍繞著輕煙。
巴掌大的欖仁葉,間歇落在柏油路上,擊著乾澀的節拍。他聽著這天地間唯一的聲響,喀……喀……喀………,蒼蒼茫茫,越來越遠,直到一個人影穿越廟埕偎近過來。
「阿兄啊,那嘸睡卡飽咧,這早起……」阿珠穿著亮黃色雨鞋,表面沾附的泥水半濕半乾,邊緣龜裂,碎花棉袖套也暈染著濃淡墨色,是剛從漁市回來?「,你稍等,我等咧去菜市仔給恁買早頓」喊話同時,腳步未歇,便自陽台底走過去了。他心中先是一陣溫暖,接著一陣遲鈍的戟刺,阿珠…阿珠……。突然覺得小腿痠麻起來,便朝門檻上坐下去。因為高度降低,視線便被那排腐朽的欄杆切割零碎。廟埕隱沒在視野底端不再完整蕪曠。陽光的色澤漸次明朗,濃霧愈散愈低,他的視線便被濱畔,隱隱自霧中升起的那座高架道路給完全佔據了。
這道路起建也已經近十年了,他搜尋腦海中那座巨大空中道路的歷史影像,最初是鋼筋一簇一簇,鬼瓜般伸向天際,然後用橫向的鋼筋迴圈綁紮起來,中心便成為一囚籠狀的圓筒結構,輪流捉放經過的雲朵。接著延宕了好些年,才又築起金屬板隔,灌注泥漿建構路墩。接著路基路面分段施工,連接起一柱柱獨立的路墩,到此刻終於算是竣工了。
十年,可以完成什麼?得到什麼,或失卻了什麼?千百人將有千百不同的答案吧。他向自己丟出疑問,卻不知道如何回答。這十年,不,或許更久以來,他彷彿只是一截割裂的旋律,從完整的曲子中間切割下來,卻不斷地被反覆播放。年復一年,他駛車周旋於島嶼南北,像候鳥往返於生存之地與繁衍之地。而一切彷彿在初次離開家園,就註定了。
三十年之前的他,那時也與這一棟樓屋同等地壯實。十九歲,剃了極短的髮,頭皮青青反射响午乾躁大氣中的,眩惑光芒。他記得,廟埕前的客運站牌,母親淚水的痕跡被海風吹散,鬈髮分岔著,糾集著,大塊大塊地飄揚,遮掩母親忽然低垂的眼神。
「阿貴,要好好看顧自己……」母親雙手交扣著他的手,熱帶海浪般的起落,豐腴,潮濕,暖和。廣場上日光滿溢如大潮。氣流強弱自蔚藍來,攜著曾經賦予他自由想像的鮮甜海味。曾幾何時,卻成為他亟欲捨離的氣息,漁港的腥摻著鹽田的鹹,難堪困蹇的少年。
「會啦,會啦……嘜擱哭啦,哭甲阿捏歹看……」他伸出右手要抹母親的眼淚,他已經是強壯的男子漢了,可能因為經年的熬夜讀書吧,他體格不算魁梧,但仍是十分矯健精實的。此行就要上成功嶺,不能再像孩童一樣地抽抽咽咽了。而且他已經是全鎮的榮耀,第一個考上國立大學的庄腳囝仔。他記得放榜後隔週,父親辦了二十桌流水席宴請鄰里親朋,廟埕中央搭起紅藍帆布篷,頂上布篷鼓盪作響,噗啪噗啪,幾乎壓過敬酒交談的語聲。布篷將光線濾成顫動的烈酒色,映射灑落,每個人臉龐都漾著紅光,大圓桌像滾滾夕照,一同灼燒起來。
「來來……來敬阿彬伯,阿彬嬸,感謝人家甲你照顧,這久囉……」
「花仔嬸,自小漢看你大漢……,來……好,有禮……」
「進財仔,你後生真鰲,真鰲讀冊,後擺讀博士,做教授啊。」
「呵呵呵………」
「敬大家,多多關照……」
鐵箍般熱燙的父親的手烙著,鉗著他的前臂,扯著他穿巡在桌椅間,原來父親還有這麼大的氣力,幾乎要讓他腳步踉蹌。舉杯空隙,他回頭搜尋,看見母親和阿珠在他的位置一旁坐著。母親正當起身,挾了一隻炸蝦,置在阿珠碗中,阿珠側轉頭,視線穿越森林似的鋼柱及人群起落向外。他順著阿珠的視線看去,廟埕盡處,漁船頂黑網布面交連迤邐,一方一方,升降參差,暗示港灣浪湧波搖。漁船更上頭是天光兀兀,綴著幾座鹽山似的積雨雲,海上的強盛對流。
他看見母親拍拍阿珠肩頭喚她吃,阿珠轉過面來,正好迎向他,紅光燦亮地咧開嘴角,笑了笑。
宴席彼時,他有些尷尬,不願面對這麼繁雜的人情儀式,幾次想借勢掙脫父親的掌握,卻總不能搖撼分毫。有一度父親鬆手放開他,雙手持杯傾壺,重新斟滿酒杯。當父親要再攫抓他的手臂時,他卻還是惦惦讓父親握住了。他知道只是需要一點自由,只是太年輕,太年輕以致來不及體會,孩子的榮耀是遠較已身的榮耀,還更難平易承擔。
此刻,他已是彼時父親的年歲了。他跨坐在門檻上,轉身面向神明廳內,看見父親的臉容,仍是長眉垂下眼角外,剃過的短髭散布脣上及頷下,疏朗笑容,澹澹平視前方。父親眼前仍是空無的未解嗎?還是已然獲得了明白。他真不知情。
「阿爸,你著要保庇阿母平安快樂,阿珠一家大小攏順利……」。
「觀世音菩薩,請您要保庇阿母……」
他自門檻站起,虔誠地望著牆上掛著的佛像,合掌在胸前拜了幾拜,深深鞠躬。彎腰時,目光起落處,他看見香爐左近桌面有些香灰灑落,便轉過身,伸手至牆上木櫃間拿取抹布,擦拭香灰。
這是母親的動作呵,突然間的領會讓他不知所措,集聚在抹布底的香灰一時沒有拿捏好,有一些墜落在黑漆桌面上,像夜裡黯淡的星殞。他使勁收束指尖,將灰燼裹進抹布裡頭。
這十年來的得失,究竟是不太明白了。父親離開人世,但他竟感覺彼此較他年少時更加靠近。而母親雖然還在身邊,反而無端地遙遠,像隔著一層大霧,只看見隱約的輪廓晃移。
哪一年開始,母親不再於除夕的傍晚,拉著籐椅到家門前頭廟埕邊,迎接他開著車,載著妻和最疼愛的內孫返家圍爐。他好懷念每一年大陸冷氣團推移,領來晴朗而高冷的季風之時,總能在暖調的暮色中,看到母親穿著黑棉襖──他買給母親的那件──恬恬坐定,雙手交扣著放在大腿,頸子微微後仰,靠著椅背,沒有急切張望,反而像一只沉甸甸的香爐,篤定地承接時光沉香撲簌剝落的灰燼,等他回來。
是哪一年,阿珠攙扶著母親,晃晃顛顛朝他逼近。眼中母親的腿脛,竟瘦得像白鷺鷥,顯得膝關節格外龐大。那雙因為家事而粗壯厚實的手掌,顫危危地抓握著阿珠的手,一小步,一小步,鞋履擦曳。
「阿母,伊係誰?」阿珠扶著母親在他身旁的椅子坐下。
「伊喔……我不知啦。」
「阿母,伊係你後生啦,阿貴啊,擱你媳婦麗雲啊。」
「沒囉,我阿貴才去讀大學啊,還沒娶囉……」
「你係誰人?」母親用蒙了一層雲翳的眼望向他,沒有深深疑惑,反而像是不在乎,像與訪客禮貌寒喧的語氣。
「阿母,我阿貴啊,你後生……」他一直深刻地記認那個無可逆轉的瞬間,廟埕上,夕陽底,迴盪著母親的疑問,他使盡力量想回答,聲音卻哽在咽喉,彷彿只能自己一人聽見。
「醫生是說記憶會慢慢退化,從最近的事情開始……生活自理能力嘛會退化,變得和囝仔同款咧。現在是還沒藥醫……」。阿珠說。
「你嘜煩惱,我會甲伊照顧。」他點了點頭,遲鈍地問「阿母……阿母,現在甘擱熟悉你?」
他沒有看見阿珠的表情,他沒有抬頭去看。他只是凝望著母親的指尖,緊緊抓握住阿珠的手,不曾稍稍鬆弛。
他雙臂扶著神明桌,右手掌猶抓著抹布,這一張越洗越薄,顏色越褪越淡的破舊抹布。他將頭放低靠近看,纖維縱橫交織,顯露出一格一格的空隙。他害怕只消手掌一瞬間放鬆,好不容易細密裹起的香屑,又會自隙縫間飄灑而出。神明桌上的寶蓮燈日夜點著,顏色像是火焰,卻又沒有火焰的明亮。燈炬之間,佛像前頭,供奉著曾氏歷代祖先牌位,木製小龕內紅紙墨字,四周木框刻著卷草淺浮雕,有種老氣的華麗,又有時間打磨過的沉著光澤。
當他的肩膀尚未高過母親的眉目之前,每個月總有些日子,清晨早飯前,他疲倦倚著神明廳牆壁,感官尚未清醒。矇朧視野中,母親背影翩韆如蝴蝶踊舞。鋁鍋中澄白米飯飽脹,紅豆色塑膠小酒杯流轉香氣,亮黃色柑子盤中堆垛成山,繽紛包裝餅乾,鬆軟雞蛋糕靜靜躺在透明塑膠盒中,像在水晶棺中沉睡的貴族,一一被母親排放在神明桌上,每盤供品插上沉香一炷,廳堂彷若浮升至仙界,用力一嗅便香雲滿腔。母親年輕綽約的身,身上薄紗衣,衣上胭紅爛紫玫瑰花,層疊,遊移,幻變,同時運臂使指,打理祭儀一切。他曾經覺得母親好神,像有千手千眼,泰然自若,穩定整座樓屋的重心。他願望的所有都在母親的掌心化為真實──安慰撫摸的手,呵護傷口的手,煎魚煎粿的,給零用錢的,緊緊牽住他小手的溫柔掌心。
彼時的他,只知道和阿珠在神明桌下捉弄玩耍,蛇行虎奔,每每被母親吼罵「阿貴阿珠出去,嘜在這亂,要耍去陽台外耍」,然而那吼罵猶原是帶著晏笑的,嚇阻不了玩入瘋魔的猴囝仔。多久以來,不再一起分擔著彼此純粹的快樂了,曾經熟稔,毫無動念區分彼此的暱切,現在卻好似隔著一道漫亙連綿的山脈,知道一切還在,都還在,卻舉手撩觸不到。父親離開之後?和麗雲成婚之後?畢業後決定留在台北工作?更早……離開家鄉北上那個午後?更早……更早?早到來不及片刻絲毫存在過。
「阿兄,早頓買回來了,叫嫂子和慶安起來喫。」門板咿歪,阿珠大嗓音傳來神明廳。他踱步下樓,阿珠正把塑膠袋內數個三明治,幾杯豆漿奶茶一一取出,整齊分區排列,桌面有細緻水漬,是方才擦桌子留下的。門縫間篩進一道晴和,掠過桌面,化成銀河,碎鑽似地瑩閃,也像那天,等待客運的時刻,在烈日下閃耀的一道淚水的痕跡。他伸手去抹,驟然卻被母親揮手格開,他垂下雙手,楞杵怔然,別過頭望向廟埕對側,廟宇飛簷上剪黏神像列位,飛龍護塔,流光溢彩。釉色斑斕的最高處,空闊,遼遠,自由。餘光中,母親以衣袖搵去風吹蜿蜒的水跡,再回頭,微笑著執起他的手,「好好看顧自己……有閒著常常轉來,啊……。」
「阿珠啊,這幾年攏是你甲阿母陪,擱要顧囝仔,實在辛苦。」他擎了張籐椅要阿珠一起坐下。
「嘸啦,應該啦,你生意作這大,哪有時間轉來陪阿母……」
「我只是感覺對你真對不住……」
「阿兄,你嘜這樣講,阿母本來就是我當照顧的,住近近啊」
「請個外勞照顧嘛是……」
「給別人顧不放心啦。」
「阿珠,你厝內擱有三個囝仔要養,往後攏是要讀大學咧,我是想講喔,這棟厝要過到你的名下……」
「阿兄,這阿爸一定要留乎你的,你是……」
「阿珠啊,」他提高了聲調要壓過阿珠「那是舊觀念囉,誰講一定只能給後生,不能給查某仔,這根本就不公平……」
「不行啦,我自己嘛有呷頭路,國雄嘛有在賺。」
「阿珠……」
「我不要講囉……」他看見阿珠站起來,把那些三明治推攘到桌面對側,拿起一旁的抹布,開始擦拭飲料外壁凝集的水滴。
「阿珠,我是認真的,嘛與你嫂子講過,她嘛真同意……」他聽見自己急切乾躁的話語。
視野扭曲搖晃著,像沒入海中。阿珠將飲料杯一股氣推過桌心,展臂抹了抹桌子,轉身向後邊陰影內的灶腳行走。他聽見水聲淅瀝,感到心室中牢牢建築著的什麼,沖刷散流開來,好冷好冷,像彼時風吹密雲推擁靠岸,大量鹹水滴騰躍起來,震顫,拍擊,沁滲,蛀蝕。
「阿兄你怎在哭,你是在哭啥?」阿珠走了回來。
「阿珠……,你已經為我犧牲這多,我實在是……。」
「犧牲啥,我哪有犧牲?」
「你應該嘛要繼續讀冊讀上去,至少要讀到國中畢業……,若不是我……」
「阿兄,你考上國立大學是一定去讀的,阮攏是真歡喜……」
「我彼時是太自私了,我……根本沒想到你,只想要離開這所在……,不然我……我可以去…讀…」
「阿兄你嘜哭啦……」
「……師專,厝內嘛也可以同時供你讀冊。我……」
「阿兄……」
「……我可以去讀師專……你嘛不用一世人只能在市場賣魚做粗工……」
他看到阿珠的溫厚的手掌邊緣模糊,漸漸變大變暗,執著一張面紙要幫他拭淚。
「我不要……」他突然一陣腦海翻騰,右手架開阿珠的手臂,左手卻無法控制地,先狠狠向左前方桌面拍擊了一下,再朝外側猛劃了一大弧,一杯奶茶翻覆桌面,蓋子脫落開來,瞬間擴散成片,在桌沿渟蓄漸高,接著失控跌落地面。
「……但我只是不想回來……讀師專就能回來教書……我不要。」
他楞在籐椅間,耳中反覆彈著一段語句,起降,ㄔ于,返覆。「真是如此……?」但他候鳥般年年返鄉不曾中止過,一次不曾缺遺……。母親數十年來,廟埕邊等待的身影又驟然浮現眼前,一年……一年……,廟埕旁的磚仔厝傾倒,變成工地堆放水泥砂袋,變成三層洋房。一年…一年……廟埕上停放著返鄉人的車輛,整齊並列,佔滿整片廟埕,一年……一年……少一輛……少一輛……逐漸荒疏。只有母親端坐老籐椅不變,卻也漸次瘦弱,漸次萎縮,籐椅顯得越來越巨大。
而一年……一年……,除夕黃昏,他驅車抵達之前的等待的時刻,母親看見了什麼,他問自己,他不知道。他從籐椅中站起,跨過大門,踏上空盪廟埕,走到母親年年的等待處,駐足,擦拭,凝睇。此刻他看見一座巨大的橋凌空俯瞰自己,以堅毅的現代的線條。西濱快速道路,沿著島嶼西部海岸筆直延伸,沿線刺穿濱海,港鎮,市墟,像工廠內的運輸線經過一處一處加工生產點,將成品運送離開。巨橋那裡曾經是漁船頂黑網布升降的港,是浮光點點的浪潮,和母親牽著他的手散步的堤岸,現在已為了興建道路而變成一塊海埔新生地。
十年可以完成什麼?成就一幕滄海桑田吧,他彷彿找到早前用來質疑自己的答案。西濱快速道路實際開通之後,他要返鄉就更加便捷迅速了,沿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轉駛橫向國道,可直接與西濱快速道路接軌。一條廣闊的空中之路,無阻無礙地筆直向前,沒有彎度無需減速。奔馳的車中,風聲呼嘯如驚,氣流渦漩如醉,副駕馳座上,母親微笑凝眄,燙成大波浪的白色髮絲像整個港灣的浪花,被風揚起,絲絲縷縷竟接連脫離,向窗外飛竄而去,化為亮澈的點點浮沫,而不斷自頭頂新生的髮顏色竟漸深竟濃。
她的頭髮仍在大塊大塊翻騰,拍擊額頭和臉頰,漲落間,深刻的皺紋和老人斑也一點一點沖刷褪去。先是一年……一年……,退回那年,她駐立站牌,看著孩子拎著行李,大步跨上客運階梯,卻不曾回頭多看自己一眼。她看著客運越來越微小,穿越廟埕,轉了個彎,沒入華麗雕琢的殿宇。
接著,一天……一天……她臉色越發光鑑潤澤,頰上長肉,頷角漸豐,退回那天,她半蹲身子,臂膀環抱著身前的孩子,看著孩子小小的頭顱上伏著可愛的短髮。她執住孩子的雙手,小小手掌蜷握間捻著一炷沉香。「來,拜拜觀音佛祖啊,乎你身體健康,平安鰲讀冊……」,感覺綿綿軟軟的小指頭好像就要融化在自己的手心裡頭,決意把自己全部的青春完完全全地託付。
他彷彿又跌入了幾十年濃密的夜裡,溯汐般不斷反覆的夢境。可是模糊疼痛的夢,卻因為白日而清晰明朗。陽光自廟宇後端向海洋的方向投射,打亮天際。廟埕間的海霧,惝恍離合,絲縷化入日暖,視線化為清晰。原本被遮住的橋墩也顯豁出現,彷彿自雲端降落人間。
啊,他的夢,帶年輕的母親一起離開,去到繁華都市,天堂新樂園。他要讓母親享福,含飴弄孫,在他獨立建構出來的完美的生活裡頭。沒有寒烈的冬季風,沒有迅速朽鏽的樓屋,不被綁縳不再拘束,沒有粗俗愚騃的村民。沒有漁市惡濁腥味,臉頰結晶的鹽粒。
「阿母現在蝦嘧攏忘記了,之前還會叫阿珠,阿珠……唉……,現在連大小便也不曉囉……,真正是變甲囝仔同款。」他回想起哪一年春節,阿珠的話語。
一瞬……一瞬……夢境持續倒退向前,她卻突然忘失了一切,腦中空無,像飄浮在溫暖的黑潮裡的一隻魚。沒有思想,沒有意識。是轉醒了嗎?眼前卻仍是一片黑洞無物,是眼瞼無力開啟?
可是心室撲搏間,她卻又能篤立地,深刻地,感受到周遭暗暗甜甜的流動,感受無涯無際的溫暖,將自己緊緊地,柔柔地包裹著。她感受到另外一顆心,無窮偎近,和自己的一起,平安湧動。
他看著眼前一道路橋,在曾經的海浪上方,穩固地向兩端天際延伸。他以後就能沿著這條空中的海路經過,高高地看這座他和母親一同生長的海鎮,廟宇,廟埕,這棟老樓屋,風景一樣捲過窗外……。
他卻突然彷彿回到了往昔,感受到和母親無比親近,再沒有隔閡的心靈。他終於可以了解,母親,為何能夠始終默默地等待著他,不曾怨歎,不曾後悔。
耳後傳來阿珠的語音,「這幾年來照顧阿母,有時候親像變成在照顧自己的囝仔同款。可以留在這陪伊,我感到自己嘛是真快樂,不會怨歎啦……」
「等咧等麗雲和慶安喫完早頓,擱逗陣去醫院……」阿珠向前走了一步,來到身側,肩膀輕輕地倚向他。他側過頭,望著阿珠寧靜滿足的眼神「……和醫生約好中午過後,就欲拔去阿母的呼吸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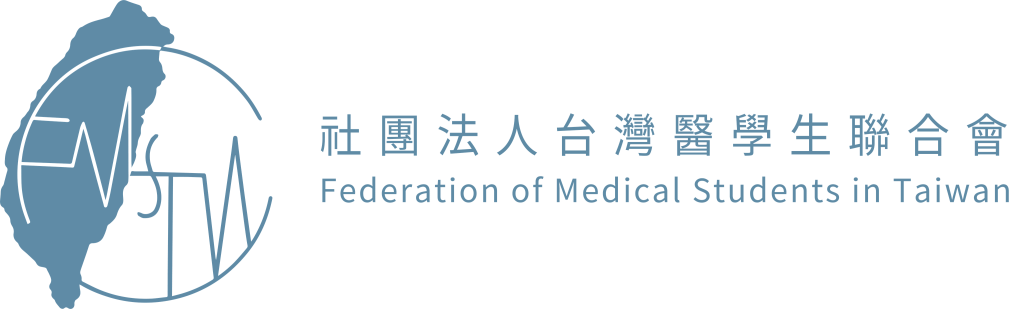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