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無意間綻開的裂口,詭媚幽魅的甬道。
當她那件黑色襯衣出現在教室他就知道了,低胸。考卷灑下,全班沉默在隨堂考之中,稚晟寫完第一大題時故作思索的抬頭,高中的講台旁通常會放張椅子讓老師置放她的縫布書袋,而當她發下考卷,巡視全班之後,她會俯身,將多餘的考卷放回袋子裡,直到翻找拿出講課用麥克風。
此時很靜,聽覺該被暫時丟棄。高度聚焦、唯一鎖定才是此刻所需(時間是否隨瞳孔放大而稍作延遲?),纖細的頸下白皙,隨著光亮減少,甬道漸次陰暗,肌膚柔軟貼覆鎖骨,然後是第一肋、第二肋;踏著尖削,象徵細弱柔媚的階梯漸次下行,就會到達目的地。
亮度此時已不足以支撐細節(於是瞳孔再次睜大),任何搖盪都陡然放大,那撞擊該是甜膩的、忸捏的互相親觸?肌膚傳遞碰撞的振頻,形似指尖劃過的輕撫。所以,若是五指捧握捏按,肌膚也會忠實反映壓跡嗎?(心臟像是被人用手緊揪了一下),那若是張嘴吮吸…
她抬頭,眼瞳上斑張的睫毛予人一種爬蟲展開背棘或鰓翼的錯覺,塗滿口唇的鮮紅豔異色澤如同警戒,她立起身來,(裂口快速收束如飛機收起艙門),輕快的拍拍手,「同學,我們交換考卷囉。」聲音嘩然在教室奔竄流動,在稚晟停留在驚嚇的當下,她已轉過身用粉筆敲啄起黑板來。
Φ
僅僅是個下午天便黑了,稚晟趴在座位上,額頭上的瘀腫散發脹熱,不時一陣昏眩。放學多時的教室空蕩蕩的,感覺不再頭暈之後,他起身走到佈告欄前,注視著那張數字人名整齊陣列,黑鉛字密麻印刷,全班的模擬考成績列表--第一高級中學三年十六班程稚晟,准考號碼7815579,(以下為評量數值)…綜合評估可錄取最佳校系:C大CM系。
忽然的起身又令他眼前全黑,腦中浮現方才體育課的情景,同學用球技徹底的讓他感到自卑後,一記富有彈性的籃板又恰巧正正砸在他的頭上。血液漸漸回流腦中,稚晟凝視自己的名字,試圖從其後一長串的無序數字中汲取信心,白紙黑字形式更予人鐵律般說服力似的。我是優秀的人,稚晟告訴自己,成績單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我應該要有自信,稚晟對自己說。
教學樓不遠處就是操場和其中的籃球場,聲音刮磨耳殼,久了成為無感,整個球場的呼吼聲雜揉在一起,變成一種同頻的強壯嗡嗡聲。
風漸漸大起來,流過教室,從這邊的窗戶到那邊,像某種透明巨大的迤長的史前海獸,灰色的天空更暗了,潑灑在整座校園的嘩啦聲響很快就沖散了球場的人群,稚晟拿起傘走出教室,下樓梯,走出教學樓,到一個街區外去補習。雨持續下,滴答聲綿密、細碎,像噤聲的哭泣。風吹拂著,史前巨獸終於從教室窗戶穿越而過,被釘在成績單上的名字不再翻飛撲拍,掙扎漸漸微弱。
Φ
數千堂如一的大教室,稚晟坐在教室後排,課程自是熟稔不已,但他仍逼迫自己鉅細靡遺的抄寫,考試訣竅不過也就是熟練,以及不去思考這些知識的用途。鄰座的同學發出一陣夾雜興奮與惡意的耳語「好鮮豔喔。」前排的女生背上,桃紅色的帶子從薄白的制服透出來,應該是被身旁的人告知,不一會兒她就穿上了厚外套。
在他低頭抄寫的同時,右前方的嬉鬧聲再次傳進他耳裡,他低聲嘖了一聲。俏麗的女學生染了頭紅髮,皮膚白皙,五官細緻,像陶瓷,坐在她旁邊的男生稚晟認得,在學校裡他總是把制服敞開搭籃球褲,打完球後坐在同學大腿上,一群人就這樣聊天打屁兼散熱,總的來說並無什麼令人厭惡之處,應該說相當受歡迎。就算是此時他對女生熱絡的摸手搭肩,與老師聊天鼓譟,也沒人覺得有什麼不妥,但稚晟就是覺得不屑,尤其是在他問了一個稚晟很早就會的問題的時候。
每當稚晟掉進自怨自艾的疑問迴圈,他都會想起她在週記上的回應:「有些人很早就具備了發光發熱的條件,但是絕大部分的人都是需要經過時間的磨練,才能陶冶散發出屬於自己的光彩,稚晟一定也會有這一刻的,加油哦!」然後再次自信起來,覺得能當她的學生真是再幸運不過了。稚晟埋頭猛抄筆記一邊偷笑,然後瞄紅髮正妹一眼。
Φ
直到在補習大樓下呆站許久,稚晟才想起父母在學校附近給他租了房子,好讓他能省下通勤時間來唸書。真是連最後一點都壓榨了啊,他想著,開始往記憶中的位置走去。夜色下燈色如火,攤販在路的兩旁無限延展,稚晟眼角掠過一旁的章魚燒攤,想像父親在另外一個熟悉的城市角落忙碌,上高中後就很少去幫忙了。章魚燒在模具中發出嘶嘶聲,飄裊的白煙燻蒸沉默的面容。稚晟終於走出了夜市區,煙塵在天際冷凝成月,他看見房東及他的父母站在門口。
「你跑去哪裡!」男人的問句其實並不需要答案,稚晟想。就算辯解也與說謊無異,說我剛剛在等你來接我,說我剛剛口是心非並且去廝混,說我剛剛如您期望在算排列組合題並調校指甲角度,尖銳嘶鳴刮磨整面黑板,或者我該說:期待與您一場鐵風暴雨、殺盡世界三千烏鴉般的爭吵,並且等您來接我?
稚晟默默的走進屋子,女人似乎說了什麼要認真啊,都高三了不要混哪。「考幾分?」來了,看來世界穩定運轉如常。他謊報了一個調整過的數字。「蛤!這麼爛唷?」男人語調誇張。「你是要全力以赴嘿,不然以後就像爸爸這麼辛苦…」也不過就是工具而已,稚晟補上固著已久的定見。不過就是作為您勞碌生活中的精神支柱,錯覺人生尚可用另外一人的成就來填補,的工具。
但演一齣例行公事並沒有耗掉稚晟太多注意力,他打量著房東,Z。「人家是C大CM系的喔。以後我們家稚晟還多麻煩你照顧了,再請你多教教他念書的方法啦。」「不會啦程媽媽你客套了,稚晟這麼厲害,以後搞不好可以來當我學弟,以後繼續住在這邊一起唸書啦。」
稚晟看著應對流利圓滑、衣著優雅的房東,熟悉的侷促感撩撥而起。那種在金屬亮面或過於光潔的地板不期然照見自己,然後馬上轉頭不看,像無意發現一件平常避而不碰的事實。所以,那會是以後的自己嗎?或者那只是個不屬於他,他這種人的境域?
還要準備食材因此父母要先回去,臨行女人殷殷補了句,「要認真念書喔。」稚晟心裡一陣悵惘,父母為了抽空來看我,回去會準備到更晚吧。他對自己的冷漠感到後悔,但又覺得咄咄逼人理應不該得到什麼好臉色。
送走人後房東直接關上門,發出「碰」的一聲。稚晟習慣性的向房東點頭示好,他看了稚晟一眼,不做任何表示便走進房間。稚晟沒來由一陣怒意,你什麼態度?看不起我還是看不起我們家?憤怒的喘息嗆出鼻腔,然後悄然散入冷冽的空氣中。稚晟默默提起書包回到房間,在夜空燃燃燈火的窗上,看見自己卑瑣的倒影。
Φ
焦躁。
隨著季節日漸炎熱,高級中學的女老師紛紛換上夏裝,自從稚晟發現新換到的座位有東西可看之後,這還是第一次因為她穿的是無袖高領使得老師彎腰而不走光而難掩臉上的失落,儘管這是不道德或至少不該期待的。
平心而論,她並沒有什麼可看性,稚晟看過色情片裡更為碩大的女人,輕解羅衫後還會肉感的彈跳。但影片裡是陌生人,現實中這個可是天天面對面,交情不錯的女人。同為想像力的媒介,後者激起的誘惑更讓他難以把持,稚晟幻想著她在衣櫃前挑選衣裝,然後在鏡前嘗試各種姿態。他更躁動了,像欲出柙的獸。
時間流過,時間又來,粉筆白跡似點點蟲卵,孵化成座位上抄寫或其他,如蛹裡的躁動不安,下課鐘響,構築完整的形才乍然崩潰。稚晟走上前去問題目,跟同學們打鬧的她笑罵著:「好啦你們別吵啦,有同學要問我問題。」嘩啦嘩啦的女聲流過稚晟耳邊,稚晟沒注意她在說些什麼,他打量著她,看得出保養修飾過的臉,在近看之下妝與影的層層堆疊,仍顯中年的痕跡;稚晟發現自己就算忍不住偷瞄也看不到什麼。
題目終究還是解完,稚晟慣性的乖順點頭:「謝謝老師。」她微笑,輕輕握住稚晟的手說很認真唷,你們其他人還不多學學,然後與其他的同學笑鬧著離開了。稚晟撇開成績相當,過來探口風刺探情報的同學,回到座位上默默的把考卷收起來,在沒人注意的角度下(實際上也不會有人注意)把手動了動,一塊方糖掉進心裡,慢慢溶化。
但他不知道的是,當下私密的甜膩記憶,會隨著封藏的太過隱密,在時間洪流下而被根本性的遺忘,他會發現已找不出最初的開始,像是找不到線頭的毛線球,但那團陰影卻不知何時,早已蜷曲糾結在時間軸上了。
他找不到那段愛戀的開始,或者從頭到尾不過是對女體的渴望?
Φ
愛慾,不容被愛者不去施愛。
猛然藉此人魅力將我擄住。
你看,他現在仍不肯把我放開。
愛慾,把我們引向同一條死路。(Divina Commedia Inferno V 103-106)
稚晟把頭放桌上,兩手環抱身體,試圖勒死胸腔裡的驚惶,及前所未有的後悔-願意去做任何一件事,只為了一切能夠重來,讓失控沒發生過,或僅僅只是能夠得到原諒。
下課時分,大家都忙著做自己的事,煩躁臨近沸騰,稚晟往教室外奔去,漫無目標的行走。路上一個聲音叫住了他。艾敏老師是個身材健壯的女人,臉圓圓白白的,腰不纖細但乳房碩大,個性嚴謹但其實對學生很好,上課總是會說些勸人行善的故事,自己路見不平的遭遇,或她兩歲女兒的趣事。
他跟著老師一起搭電梯下樓。艾敏老師圓睜著眼,試探的笑,這個平常總是不多言語的學生她有點陌生,但看得出是個認真的乖學生。稚晟最近讀得怎樣啊?還好啦。有想要推那間學校嗎?最近聽說V系很紅耶!噢,對呀。稚晟心裡慢慢有種能喘息的感覺,談話讓他可以假裝,假裝自己仍是平常那個高三生。
Φ
「稚晟你給我過來,在這裡坐著。」
辦公室的小客廳,稚晟記得在與她關係尚好時常常進來,不過這種情況下倒是第一次。高中三年來稚晟沒看過她這個樣子,也不知道原來一個女人可以發出那麼大的音量。
「我去打電話給你的父母,跟他們說說你對老師是什麼態度。」
「我又沒有惡意。」
她沒有答話,逕自走回她的座位打電話。
上課鐘響。一個老師問他:「你不用去上課嗎?」
不久,稚晟看見他的父母在廣場,他們也看見稚晟,向辦公室過來。
「你在幹什麼啊?」母親小聲斥責。
「我又沒有怎麼樣啊,老師她忽然就對我發脾氣。」稚晟小聲辯駁。
「你吼,書不好好唸,害我們因為這種事被找過來。」父親說。
「等老師來再講啦。」
他們坐著等待,四處望著下午陽光透入的辦公室一角,進出的老師彼此高聲談笑,有的會好奇的看他們一眼。
「稚晟的爸媽不好意思,把你們找到學校來。」
「不會啦哪裡哪裡,請問我們稚晟怎麼了?」
「就是啊,你知道,高三的學生,他們的壓力都相當大,會變的很喜歡來找我聊天,這個沒有關係,身為老師我覺得我可以做到幫他們排解他們的課業壓力。只是我發現稚晟的問題好像不是這樣…」
「噢這樣老師你嘛真辛苦啦。」
「不會啦。稚晟他啊從以前就都很認真寫週記,只是最近的週記會有點奇怪,會出現比方說『老師我很哈你』這樣子的句子。」她在空中點了六下。「當然我是不能確定他真正的想法啦,他也都會上課前幫我擦黑板或是幫我提包包。」
「我是會覺得說,當然我在週記也有寫啦,愛情喔應該是要兩方都享受跟愉悅才是對的,那身為他的老師我也只能做到跟稚晟是處於師生間的關係。」
「稚晟你喜歡老師喔?」父親用打趣的聲音問。
「剛剛稚晟質疑我說,如果我有空跟其他同學打屁聊天,為什麼沒有先幫他改他的作文?我會覺得說,」她提高音量,「他已經管到我頭上來了,我會覺得說,以我的立場,不能容許這樣的事情,所以也是想說今天把你們找來這樣,把問題解決這樣子。」
「我沒有質疑,我只是問問。」稚晟低聲說。
「稚晟你這樣就是不對。」父親幫腔。
「稚晟你這樣不行耶,人家老師已經結婚了啊。」
「對啊,老師都這麼老了。」她換成嬌柔略帶鼻音的聲調說。「你再這樣子,老師要跟你保持距離了喔。」
「好啦老師這樣子我們知道了,我們會好好跟稚晟聊一聊。」父親說。
「稚晟平常都很少跟我們溝通啊,問他他都說『沒事』。」母親說。
「那就這樣子。稚晟,除了課業方面的教導,老師沒辦法再給你任何回饋了唷!這樣也許很殘忍,可是對你是最好的。」
「那還請老師不要影響到稚晟課業上的需要。」
「這方面請程爸爸不要擔心。」
一切終於結束,稚晟抬頭發現辦公室除了他們以外空無一人,窗外黯淡為紫色。
Φ
桌燈白光照著五顏六色的講義和其上的筆記注解,熾亮反光使人有種身在沙漠的錯覺,稚晟啪的一聲關掉桌燈,走進浴室。望著鏡子他告訴自己,哭吧,這樣會好一點。他望著自己,嘴角抽搐,眨眼想擠出幾滴眼淚。然後啪的一聲,他趴在洗手台咯咯咯的大笑。笑得前仰後合,笑得咳嗽並迸出了眼淚,啊啊你啊稚晟你真了不起,你這好笑的悲劇。
門外傳來一陣大力敲門聲,稚晟將臉恢復成一張面具,打開浴室門,回應他的是微漾淡笑的臉,Z晃了晃手中的鑰匙「你等下有任何行程嗎?」稚晟稍微鬆開挑釁的眉毛,「沒有吧,怎麼了?」。Z又晃了晃手上的鑰匙,笑容弧度更大了。
雲豹發出噗噗噗的轟鳴聲和明顯的振顛,「檔車帥歸帥,但是載妹會被嫌難坐還有沒地方放東西;但換個想法,」紅燈停下,Z轉頭「扣」的敲一下稚晟的安全帽:「騎檔車這種男人的浪漫,不趁沒馬子的時候享受更待何時呢。」戴安全帽看不見臉,稚晟卻不由得覺得溫暖,自從辦公室的會談,還沒有人這樣若無其事的與他聊起這些,稚晟只記得被塞入腦中的都是些帶著不屑的句子,學生做好學生的本分就好,以後有好工作要什麼女生沒有。
夜晚冷的讓人哆嗦,蚵仔煎在鐵板上發出嗶剝的聲響,Z呱啦呱啦講著一個又一個真假難辨的低級八卦。
「這個故事是關於強者我朋友。他呢,玉樹臨風,家財萬貫,人帥真好,說話又風趣…嗯你要覺得我就是強者我朋友我也不反對啦,不過你等下就知道為什麼我不想承認了。」
「就是有一天啊,夜黑風高的月圓的晚上,我朋友跟他馬子吃完大餐後,就不意外的前往某家賓館,吃真正的大餐。」
「他馬子呢,身材火辣又高挑,重點不是高挑,也不是臉不好看,不好看枕頭蒙起來就好。而是她有一種淫蕩,你知道吧?那種淫蕩到骨子裡,你應該懂我在說什麼吧?呵呵呵…」
稚晟想到了那些下午,不過他搖搖頭,問題並不在於淫蕩,也許在於無可自拔,因無可自拔而淫蕩。
燠熱而沉悶的午休,座位上睡覺的學生像一座座雕像,空座位的主人早就不見蹤影。時間凝固靜止,像趨於平衡的沙漏,只有些許粒子落下滾動--電扇依然轉動著,地上飄落的考卷發出沙沙的聲響,盆栽的葉片在陽光下呈現金黃,隨風輕微搖動。
鐘聲響起,沙漏重新翻轉,稚晟聽到那把輕脆悅耳的女聲割破耳膜:「同學起床囉,每次我都要到你們班來叫床!叫你們起床!」同學們發出唔嗯難辨的無意義音,有的揉著眼,有的起身去洗臉,沒有人意識到剛剛她說了什麼。稚晟調整坐姿,厭惡與興奮強烈的讓他無法自己,那些傷害殘留的疼痛感掐刺著他的心臟,腦海裡旖旎淫麗的幻想全力奔馳了起來。
「一進到房間之後,他們就嗯嗯艾艾的從門口一路激吻到床上,褪去彼此全部的衣裝,除了女友的決戰絲襪還有細跟高跟鞋。」Z講的口沫橫飛。
「前戲做足,他女友於是將他撲倒,坐上去搖了起來。」
意象在稚晟眼前浮現,她渾身白皙,除了幾綹長髮披在身上,陰影般飄動,她弓著身,她張著嘴,(沒想到女人音量可以這麼大),意象搖晃越來越劇烈,直到世界震顫了起來。
下課鈴響,同學們嬉鬧,有些則趴下睡覺,稚晟站在自己的座位旁猶豫了一會兒,最後仍一步步地走向講桌,問一個自己早就知道答案的問題,儘管她都已經表現的非常明白。儘管她會冷落、傷害他,稚晟仍然抵抗不了接近她的衝動。他不清楚自己在想什麼,也許是期待某一次接觸的結果有所不同?也許是對自己的意淫感到懺悔?但其實都一樣,他們早就知道了。
她並沒有看稚晟,盯著考卷就開始講解了起來,中氣十足、句子簡短、像在罵那張考卷。不一會就講解完畢,稚晟尚未意識過來,她把考卷塞給他,轉頭為下一個同學解題。是錯覺嗎?是錯覺吧!我又對她不公平了,是嗎?他看著她注視著那位同學,微笑的講解,為什麼僅僅是差別待遇可以這麼難以忍受?他想起辦公室裡她當著父母的面嗆下的那句:「既然你愛比較老師對誰好,那我就是要讓你比不上。」稚晟衝出教室,漫無目標的在校園遊蕩。
忽然稚晟發現熟悉的身影,艾敏老師看見了他,卻只是加快腳步,稚晟不由自主的趕了上去,兩人一起進了電梯,稚晟擠出微笑想要攀談,老師卻不想搭理,顯得拘謹排拒。稚晟不敢置信的看著眼前總是負有使命與熱情的老師,記憶中乖巧溫順的自己,竟也會受到這樣的待遇。他想像她對艾敏老師說,你不迴避他,他就會纏上你。「瘟神」,他浮現了對自己的最佳註解。
電梯門開,老師快步離去。
「那天很奇怪,我朋友他自己是很有感覺,但是他的分身卻提不起勁來,於是我朋友示意他女友下來,打算換成後背式再戰。」
「而你知道的,在柔軟的席夢思床墊上,高跟鞋是很難保持平衡的。於是就這麼剛好,在重心不穩之下,尖銳的高跟鞋就這麼不偏不倚的,刺在他的寶貝袋上了。」
「我朋友大叫了一聲:『幹!!!!!』,那裡呈現了輪胎被刺破,軟成一坨的狀態,他劇烈的在床上翻滾,口齒不清的罵著髒話。他女友在一旁急得快哭了,問他要不要幫忙含,但他只是一直罵著混雜著呻吟的髒話。」
兩人咯咯咯的笑著,想像著那幅香豔刺激卻又逗趣的畫面,稚晟心裡又浮現了那個念頭,儘管自己憂鬱、悲傷,任何人都看得出來,但任何關心他的詢問,他都不能說出緣由。他渴望有人可以分擔痛苦,但他不能,說我愛上了老師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要是在班上傳開,稚晟無法想像會受到怎樣的訕笑(他們會接口:喔,你想把老師然後被打槍,瞭解),以及受到她更糟的對待。
也許,這次會不一樣嗎?
稚晟開口叫了房東一聲,房東仍然在笑,眼旁一條條的魚尾紋,他抬了抬眉毛,示意稚晟說下去。
夜更深了,鐵板不再發出嗶剝聲,冷卻成一塊死寂的鐵,Z將安全帽遞給稚晟,他默默的接了過來。雲豹發出噗噗的聲音,緩緩的駛在清冷的道路上。許多年後,當他再次聽到陌生的晚輩有著跟自己一樣悲慘的故事,他以為自己能夠給予建議,甚或只是一些鼓勵安慰,但他發現其實不能,性並沒有錯,愛更沒有,但萬一錯了,就是不可逆的自作自受。沒有人能給予他們救贖,就算是他們彼此也一樣。
Φ
他坐在教室內,機械式翻弄講義考卷,再幾分鐘,學測就全部結束。外面傳來鼓譟與奔騰,課本不時飛落樓下,紙張發出撲翅的聲音,他感到雀躍,理應感到如此的,卻又覺得不真實。
鈴響,監考的竟是她,學生繃緊與興奮的情緒圍繞著她鼓噪,(也許趁勢摸一把,反正以後永不相見?)他坐在座位上盯著桌面,不一會兒上面就多了張考卷,他將自己埋首於內,沙沙筆聲久了竟成一種無感,分不清是筆刮磨紙,或是她的長裙曳地擺動的聲音。
考試終於結束,校園像是炒熱的鍋,稚晟再次湊到講桌前,都要離別了總可以好聚好散吧,他心想。她身旁圍簇著滿滿的同學講笑打鬧,沒人排擠稚晟,稚晟擺出笑臉想要融入話題,但話屢到口邊卻又住了口,她整理好東西開始往門口移去,一堵人牆伴隨著笑語跟上,稚晟站在原處目送,然後回到座位收拾東西。
他馬上就追上了他們,吊在後頭保持距離,「尾隨」,他想起這個常在新聞上看到的詞,覺得想笑。同學們陪到辦公室門口就道別離去,她抱著考卷獨自回到位子上。
他吸了口氣,緩緩的走向老師的位子,越來越近,她依然低著頭做著自己的事情,悠悠的開口招呼,稚晟有什麼事嗎?沒有啊,想說要畢業了,來跟老師說再見。嗯,她柔柔應聲,沒有抬頭。
最後的轉身,他帶著一種悲壯的姿態離去,忽然發覺沒有人在乎,沒有人在乎,辦公桌旁的隔版貼滿學生送她的卡片以及謝師宴的相關事宜,(是啊,所以沒有人在乎,誰在乎呢?就快走吧快滾。)
他乎地迴轉身軀,她尚未反應便感到頸部一記重擊,他望著她倒在辦公桌上,恐懼傳遍全身,然後被狂喜掩去,他抱起她,(她長髮蓋過額頭,輕輕搖晃,臉淌著血),像擺弄一件玩具。嬌小的她竟讓他抱不動,為了支撐重量,他用大腿去頂她,腴軟的感覺傳遍全身,強烈的像是要印出輪廓,像壓路機過碎玻璃,震碎過往日子裡無盡的想像。撩起的裙襬露出其下的一節小腿,黑色絲襪勒出小腿曲線,高跟鞋掉了,兀自倒在腳旁。
門口傳來一聲驚叫,許多人跑動叫嚷,他望著外面,心臟劇烈吵動;他終於將視線轉回老師身上,輕輕抱著老師坐下,溫柔地撥開垂曳頸項的長髮,甬道近在眼前,那無意綻開的裂口,(白皙的肌膚上有小小的坑疤和紅疹,都是以前沒發現的,怎麼可能有學生發現呢?),不可言說的竊喜,和必然的毀滅。腳步吵嚷蜂擁靠近,他面色平靜,能將他征服的只有一處,決定他命運的並非此刻,早在窺視的第一眼,就已不可逆。
眾目睽睽下,他打開了甬道,俯身下去,湊上嘴吸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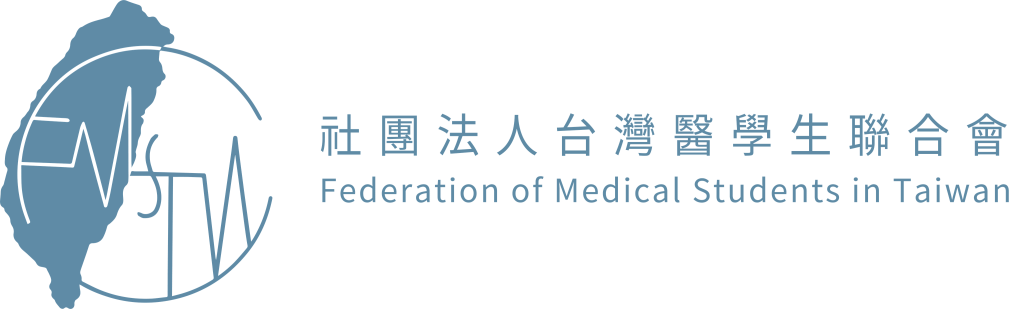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