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要澄清的是,「長大」這件事情是很弔詭的。當然,你不可能早上一醒來,突然看到鏡子裡面有一個完全長大的你自己笑著和你說早安。沒這回事。長大總是緩慢的,感覺不出來的,從別人的眼光反映出來的。父母忽然告訴你,門禁時間向前拉了兩個小時(當然你會抱怨,但是那時你還沒學會叛逆,所以你最後還是妥協);周圍忽然有些朋友開始收到情書(哥兒們挺直胸膛,用很不屑的語氣說:「喔,那個女的啊」,但是你看到他在數學課時一筆一筆慢慢寫著給女孩的回信);然後你忽然發現,「決定你一生」的聯考就在眼前,很多人開始「關懷」你對未來的安排。能有什麼安排?你根本都還沒準備好,就已經栽到這個「長大」的漩渦裡面了。
我沒辦法避免的先提到「剛長大」的時候。剛長大的時候,我們對某些事情還很敏感。我很慶幸已經過了那個年紀—聽到老師憂心忡忡地提出「長大」這個具有正面意義的詞彙時,男生會吃吃傻笑著用手肘頂來頂去,一邊對女孩投去曖昧的眼神;女孩則一甩頭髮,從鼻孔中哼出長長一氣,雙手抱胸或翹起腿。那個時候,我們的世界觀建立在以下三點之上:愛情是在東京鐵塔上,不眠不休地往下看整城的燈光;人生沒有這麼困難,站在那個支點上,就可用槓桿舉起地球;不管別人跟你說什麼,只要自己相信的就是真理。
剛長大的時候,我們什麼都不怕。
長大當然代表著我肌肉的壯健和成熟—我指的不是摔角選手那樣的大塊肌肉。家庭旅行的時候,我不再能跳到汽車後座,等著老爸發動引擎了;我得負責一部分的行李。簡而言之,只要花色太炫麗、不適合「男人」提,偏偏又很重,沒辦法給老媽一手拎起的行李,通通本人包辦。是的,生在一個沒有兒子的家庭,我發誓我的三頭肌比班上的男同學還快膨脹起來。新年有一齣固定的戲碼是這樣的:「來,小乖,把這幾箱東西搬到後座,給你三伯、四姨和五叔叔的。別忘了要穿窄裙,坐姿要內斂一點……妳說搬完再上樓來換?時間不夠啦,穿著就搬下去了真是的……」同時是個淑女和搬運工?這可不是迪士尼的「小姐與流氓」。這是「小姐,請成為流氓!」
長大讓我們變得多愁善感。我還能記得,有一次獨自走在書店街上,像是老道的掠食者剛打完牙祭,沒有胃口了。停在二手書店外翻閱小說。忽然店內傳來許美靜的「城裡的月光」。我呆呆地放下書本。原來是這樣的,我對自己說,原來「為賦新辭強說愁」是這樣的滋味……我的視線甚至還沒瞥到尖塔的頂端,我已經在為我將看到的風景犯鄉愁了。但我真的沒有愁過麼?真的沒有人在我成長的年代軋下一些深深淺淺的軌跡,然後完全地消逝於空虛?十多年的懵懂年代,十多年的記憶扉頁,真沒有哪個逗號句號可以讓我愁過幾個秋夜?
長大特他媽的還真複雜。
感覺上我才剛流血流汗走進大學,忽然就有人彈著吉他在唱「今年夏天」了。那完全是個意外。我在五樓的美術教室畫水彩畫到眼前都是光點飄來飄去,步履蹣跚地走出教室。外面已經是夕陽遍灑了,快要沉下山去的太陽,正在往外拋擲一顆又一顆的金色子彈。我閉上眼睛,聽到那些子彈叮叮咚咚地跳到地上,再反濺起更多細微的聲響……然後,我就聽到了,吉他那種特有的音色。生下來就像是流浪的代言人,不管是年長年少,每個人的旋律—即使是歡快的—都有點執著的感傷。我在「民歌高峰會」上聽到葉佳修在昏暗的燈光下唱著「流浪者的獨白」時,便被吉他的聲音給誘惑了—來自中古,吟遊詩人特有的魔力。月夜人變成了狼,在懸崖上激情地詠唱寂寞;櫻花旁邊少女把脆弱的蝴蝶交給軍官,等待一個悲劇的結局;在馬德里弓箭穿過了精靈的胸膛,銀色的血液潑灑之後成為一樹低矮的曇花……
我靠在柱子旁邊,讓回憶慢慢地流動。如果畢業了,這間學校該怎麼辦?說來無奈,我真的很擔心學弟那天真活潑的樣子:他們總是把期末考忘掉,直接把日曆翻到春假服務隊出隊的那一頁,燃燒的是全然熱血而非現實考量;談到不及格的成績時難過的把臉皺得像包子一樣—往前看吧,寶貝,你知道的,你人生中不及格的事情還多著呢,而且多數比微積分考試重要多,也糟糕多了—還有那些我來不及教你、也不應該由我來講述的事物:包括怎麼和老師反映作業的「死線」太靠近期末考(要先苦苦哀求然後說之以理,比例大概是七比三),怎麼保護自己不要受太多的外在評語傷害,要怎麼在情人生氣的時候用微笑和玫瑰度過困擾……唉,想當年我不是也這麼熬過來的嗎?總是要撞到荊棘,才知道失血過多是什麼感覺。一點點「苦」的必要,讓人的兩鬢多些灰白,然後人生的滋味才會圓融起來。
待會兒。想當年?我什麼時候這麼老成了?
想想其實我還蠻喜歡長大的感覺。第一次被朋友背叛時,我趴在床上哭了一整夜,連看鏡子都不敢,深怕自己太狼狽。後來實在哭得煩了,抹抹眼淚、有點氣憤地用力拉開窗簾,天上所有的星便一起映入眼簾。雖然只是淡淡的光,閃閃爍爍,退縮地在夜空中吞吐著自己的亮度。心底最深的地方,忽然點起了小小的蠟燭,跟著星光一起搖搖晃晃的,把夢照亮。要快樂啊,我對自己說,不管碰到什麼事情,總有屬於自己的星光,在某個角落撐起整個遼闊而寥落的夜。
有很多人用更痛苦的方法學習「長大」這回事。推門進去的時候躺在床上的赫然是曾經拖著兩條辮子滴著鼻涕滿街追著我跑、彷彿還是昨天、永遠不會長大的小表妹。稚嫩的臉上還帶著柔軟美好的青蔥。青蔥的不只這個。幸運草般的圖案印在灰色的長袖運動衣衫上,正好就是小腹隆起的地方。照超音波的時候幾乎不敢看她的眼睛,而嬰兒成形的一瞬間她失聲痛哭。我將手伸過去環抱住她。她紅著眼圈卻是如此倔強地一言不發,拎著包包昂首闊步地走到外面去。第二天晚上姨丈打來興師問罪時,大概是我這輩子引用最多次「醫生病患保密協議」的一通電話。在他間歇性地咆哮之中我聽到了背景音效是抽抽噎噎的女人哭泣,不曉得是表妹還是姨媽。
幾個月之後我去吃滿月酒。這是不是幸福快樂的結局我不曉得,表妹看起來蒼白而疲倦,除此之外還有怵目驚心的木然。在全黑色的禮服包裹下顯得如此嬌小。這時我忽然發現,有些事情不管怎麼處理怎麼努力,最後的結果必定仍然通往悲劇。就像拉斯維加斯的賭局。靠的全然是新手的運氣。我抱過小孩時她不滿地踢動著雙腿,表妹趁這機會抽掉了墊在胸部讓嬰兒吐奶的領巾,一臉認命地扔在垃圾桶間。
表妹把小嬰兒抱回去時,表情在短暫的幾秒之間又充完了電。簡直比我還堅強,經過不間斷讓手臂裡那隻小孩扭動哭鬧和詭異的味道散發,十分鐘內已經抽乾了體內近乎一半的精力。連續兩堂高中數學課都坐不住的小表妹居然能以源源不絕的愛心來包容這種無法言語溝通小東西,這可說是一種千錘百鍊、被迫高速發生的成長?
就在沉吟的此刻我看到了遠方熱切的眼神。約莫三十五歲上下,穿著價值不斐、頗有品味,身旁跟著一個已經地中海微凸的男人。我頓時知道那是種渴望,就像是九歲那年我盯著姊姊拿著新四驅車模型的眼神。想要得不到,也許是人間不停循環的折磨,一如克勞力地獄那樣,最深的折磨其實是年復一年不斷的排隊,永遠不知道前方是什麼,永遠也拿不到最想要的賞賜。一個人垂涎已久的珍寶也許是另一人一有機會就會丟棄的草屣。這約莫也是驅使人不停長大變強的動力,跟在永遠抓不到的流星後面跑,希望在那萬分之一的機會中抓住燦爛的瞬間。
婚禮、喪禮是感情迸發的最佳場所,但最能讓人感覺到歲月不留情軌跡的莫過於同學會了。當年念的是女校,來的卻有一半是男性人口;誰胖了誰瘦了誰又窮得快活不下去了。大家都很有默契地避過了以現況互相競爭的話題:當年在一起同窗共墨時就已經無聲而友好的廝殺的你死我活。但是明顯的,我從樓梯上下來時,從那個鷹眼俯瞰的位置,我可以看出誰是真的被社會打磨的老了、誰又是意氣風發還是無所畏懼。曾經高昂熱血的變成淺斟低吟,一句話出口前都要考慮半天,到最後乾脆閉口緊抓著飲料杯不停附和著點頭;曾經溫柔害羞的0變成侃侃而談,彷彿整個桌面都是她每日晨報的會議桌,殺伐馳騁酷似天遣貞德;曾經仙風道骨、不食人間煙火,風吹來都要折斷柳腰的「小林妹妹」,不停吆來喝去、控制她那一雙像失控火車般東奔西闖的雙胞胎兒子,軍令如山恰似王熙鳳。
我癡立的時間過長,擋到了後面的人。直到她拍拍我的肩膀,這才回過神來。短髮及肩,肩挑古齊新包,當年高中還算個能談得來的朋友。她跟著我看了幾秒,然後吐出一口長氣。
「你還記得年少時的時光嗎?」
「是啊。」傻的我都不想要再提了。
「你知道嗎。」她嘆了口氣,靠向我,壓低聲音像是正在分享什麼了不得的秘密。「我願意付出一切一切。回到那個時候。」她的手習慣性的下滑拍打口袋。我遲了幾秒才想起,她是在確認口袋裡還有沒有菸。我別開眼睛。
「不。」
「什麼?」
我聳聳沒有解釋,而是走下樓加入他們。
我還記得年少時的夢。我所有的夢。包括停止戰爭,讓家人永遠健康,環遊世界。這都要求我長大。長大,變得足夠殘酷, 足夠強壯,然後將夢想堅實成真。
回憶是很美。但是我終於能憑藉一己之力有所作為。
是,不能再回頭了。就像我現在做的,敞開雙臂,加入群眾,然後融化在微笑、淚水和對未知未來的好奇之中。像是闖到了敵方最後一排的西洋棋兵,選擇轉成了皇后,成為整張棋盤最有前途的明星。這一盤棋會下得如何,全在我的決定之中,而我早已躍躍欲試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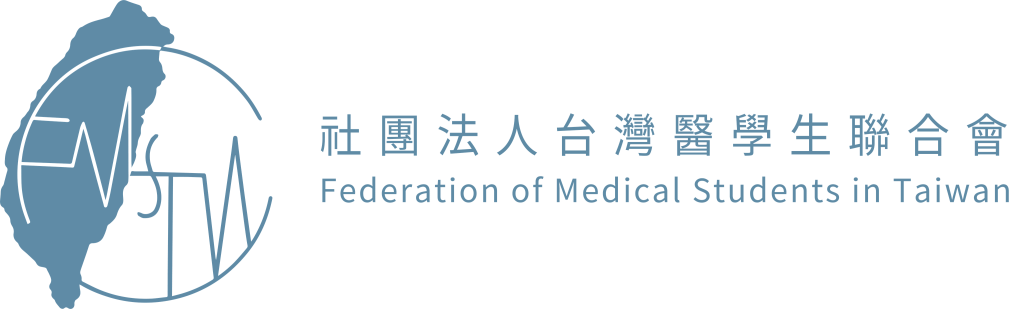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