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小說組評審獎]健二《變態》
「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不太能了解你吧。」室友小彬一邊咀嚼自己做的咖哩炒麵,一邊拿叉子直指著我。
「哎呀,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雖然很感激小彬每個周末中午都會免費幫我做午餐,不過他這樣說我還真有點傷心。
「小心玩火自焚,連學弟妹私下都會講,你也不是不知道。」小彬倒了一點無糖檸檬汁到我的小叮噹馬克杯。
「由他們去說,難不成我還要一個一個去告解?」我喝了幾口檸檬汁潤潤口,準備來吃烤得有點焦的奶油餐包。
「觀念不同,不講了。」小彬語帶鄙夷地說,我想反駁,但後來選擇安靜吃完這美味的一餐。
「剩下一點番茄高麗菜湯,我喝掉喔。」我把空無一物的小鍋子放到洗碗槽。
「你下午有事嗎?我想去好事多買巧克力、冰淇淋和起司餅。」小彬一個禮拜有三天去游泳池報到,這點零食還胖不了他。
「我等等就要出門了,你要不要找阿凱跟你去?」我邊把沒吃完的檸檬原汁和生菜放到冰箱裡。
「還要出門啊!禮拜一不是要考肝膽腸胃科?」小彬眉頭微皺、嘴唇上翻地說,老實說我並不喜歡他那表情。
「我有念了。」我輕輕把房門帶上,「換一下衣服。」我對著房門說,也不管小彬是不是聽見了。
我不想讓小彬看見我出門時提了個紙袋,萬一他問起紙袋裡裝了什麼,我可不敢說那是我高中時代的卡其色制服。並不是介意他又會對我說什麼刻薄的話,我只是想求全我在這公寓裡建立的平凡人般的安穩生活。
「阿凱說他可以,那我先出門,掰掰!」小彬的聲音聽起來很遙遠。
隨著小彬把鐵門帶上,我把房門打開,讓客廳落地窗的風吹進來,接著坐回蘋果筆電前,打開臉書的分身帳號,過濾掉不必要的廣告訊息,再依序回覆朋友的留言或照片,最後打開私訊,將老陳的手機號碼輸入我的手機通訊錄裡。
我看向落地窗外的行道樹景,決定今天外出就穿前幾個禮拜新買的白Force,那是一種轉換的況味。
秋天的艷陽將Hollister白色T恤的清爽風情詮釋得相當好,配上淺棕色的工作褲和板鞋,我知道走在重慶南路的自己將成為某種不具名的故事形式,動態地流轉在人群之中。
「你在哪?」老陳透過電話不客氣地問,連名字都沒報上,身為小學老師也太不懂電話禮儀。
「我在三民書局,看雜誌忘了時間。」其實我只是站在雜誌區,由左到右、從上到下,一本一本地在心中默念雜誌名稱。我本來是個守時的人,但我得學著惡作劇。
「我在北二門,你現在走到轉運站,在那邊等。」想到老陳又要頂著他那滑稽的鴨舌帽走在街頭,我不禁覺得自己可恥又可惡,不過這也無可奈何。
「今天要去哪?」老陳不知道哪裡開了竅,竟弄了頂假髮遮掩雄性禿,還穿了套體面的西裝,我直盯著他問,也不管路人怎麼看我。
「就附近吧?重慶南路或中華路……」老陳放下沉重的旅行袋和太陽餅,用他飽受粉筆侵擾的富貴手擦去額頭的汗水。
「今天我一群朋友約去京站看電影,好像還要去Friday吃晚餐,我為了見你,還推掉這個約。」我裝做沒好氣地說,「不管,反正這附近不行。」
「那仁愛路那邊呢?」老陳皺了眉頭,我抓準天氣熱,他也是不耐煩了。
「隨你吧,我招計程車去。」我腋下都汗濕了。
「忠孝敦化捷運站。」我看見老陳腆著肚子,一面用戴著俗氣金錶的左手拍掉肩上的頭皮屑,一面張大嘴指示面戴黑框眼鏡的中年司機,我好像聞到煎餃和大蒜的味道。
「現在後座也要繫安全帶。」我嫌棄似地說,同時挪動身體緊倚計程車後右側的車窗。
「哎呀,這安全帶怎麼……」老陳慌張地拉扯左側的安全帶,孰料安全帶拉到他皮帶扣那兒就卡住了。
後來黑框司機在駛過新生高架橋前於路邊暫停車。
我百無聊賴地拿出前陣子才拿到的hTC J,翻看通訊軟體,發現吉娜表姐詢問等會兒是否共進晚餐,地點在101八十五樓的隨意鳥地方。
『還是只有週四晚上比較有空耶。』我即刻回覆。
每週四見習結束後,我往往蹬著迪奧黑色尖頭皮鞋搭捷運到松江南京,等吉娜表姐開深藍色奧迪接我到她家吃她煮的家常晚餐。
我國一的時候母親再婚到香港,那之後直到高三為止,松江南京的公寓取代原本在公館被稱為『家』的建物。我本來很感激吉娜表姐待我如親弟弟般的悉心照顧,但在我高二下的某天晚上,吉娜表姐與我說:
『前陣子我和男朋友分手了。』我還記得那天她穿開襟白襯衫,我不可能沒看見她內衣的粉色花邊,『你和他都是雙子座,你知道嗎?』
那天晚上我才知道吉娜表姐體內還住著一個女人,她逼迫我變成男人。
之後我開始晚歸。補習結束後,我帶著渾身的罪惡感和逞強的眼神,從館前路閒晃到西門町,墨綠色書包與卡其色制服散發淡淡的汗臭,我覺得那就是我待價而沽的仲夏青春——但那是不公平的交易,我往往覺得我的眼淚被賤賣了。
「你這根本就是鹹魚乾味兒!」老陳脫下我的白Force,仔細嗅聞我穿了兩天沒洗的黑色踝襪。昨天我還依著他的要求,小組討論課一結束就飛馳到運動中心室內場和幾個朋友打籃球,「果然有好好在運動哪。」我聽見老陳如此說,喉頭一陣酸楚,不覺把頭別過去,茫然地注視昏黃燈光輝映下的俗氣壁紙。
「不開心啊?」我看到老陳齒縫的韭菜。
「還好,最近壓力大。」我裝做漫不經心地仰頭看天花板。
「等會兒去阪急,給你買雙新鞋。」老陳撫摸我的腳背,「還是你有沒有缺襯衫?你身材這樣好,怕是不用修改也有合身的。」
「最近不缺襯衫。」我坐起身,從老陳手上縮回我的光腳,「晚上要吃什麼?」
「晚點我大舅媽約我到永康街喫飯逛街。」老陳看著被單的縐褶,好似在照鏡子。
「你又來了。」我揀起丟在床另一邊的踝襪給自己穿上,「冷氣好強。」
「我一直跑台北家人也會懷疑。」老陳將自己下滑的皮帶上提。有人說男人進入中年後連外貌都會和父親越來越像,我猜想老陳他父親幾十年前是否也慣性提著一袋秘密,透過旅行一再叮嚀自己莫忘初衷?
「那等一下我自己搭捷運。」我打了個哆嗦,立馬將敞開的卡其色制服上衣扣上。
「我們等等先去阪急,買好了我再送你上車。」對於老陳不安分的手,我閃躲了一陣才屈服。
「看到你稚氣的臉,真想寵愛你、又想蹂躪你。」老陳究竟知道不知道時效一過,魔法總是會消失?我用我自己都害怕的演技,走在老陳前頭,挑了一切他看得順眼的衣物和鞋令自己換上。每當這個時候,我都想起仙履奇緣的故事,然而我不像仙杜瑞拉在體制內勇於夢想自己的夢想,我總覺一踏上捷運的我,就像下了戲的三流演員,隨一張張磨損的倦容,啪答啪答地在極端間忖度無關緊要的抉擇。
在忠孝新生站換車後,我戴上耳機,用音符築起銅牆鐵壁,再從波士頓包裡拿出臨床診斷學的共同筆記,直接翻到重點整理那頁,複習和腸胃科學相關的身體檢查細項。
我何必如此兢兢業業?手機裡存放的歌曲盡是高唱夢想、希望與勇氣的泡泡糖歌曲,我有時認為這是表露心跡,卻也不否認這種舉動的諷刺性。或許我真是個好行小慧、無所用心之徒罷。
『晚上有空的話來Commander,福晉今天洞八放假囉。』王爺捎了封簡訊。
『在買水果,柳丁很便宜,你要的話趕快回傳,我多買幾顆。』正當我要回王爺簡訊時,小彬又傳來這樣的訊息。
『禮拜一考試欸,不能喝啦,哭哭。』我重打了幾次才送出。
『好喔,幫我買個一斤,明天我打综合果汁。』我本來不想麻煩他再多買的。
怎麼說呢?像這樣的晚上,我不太想再見到誰,就算是住公寓對面的那位在麥當勞上晚班的俏麗女大生我暫時也不想看到。我知道她晚班下班後會到頂樓抽菸,某個凌晨我喝茫,正要到頂樓拿換洗衣物準備沖熱水澡時,竟看見她瞪大雙眼,用菸頭灼燒小傑籃球褲的褲檔。
『你等一下,』女大生又哈了一大口,『你要多管閒事告訴你室友,你就不是男人。』我罩子放亮後才又看清楚她身穿尺寸過大的男用襯衫,下半身僅著一雙顯然過大的鴛鴦配色Kobe 7,我隱約明白小傑這幾天不回來睡覺的原因,他只說要回南港家裡好好讀區段考。由於大四考試實在太過密集,若非那晚走上頂樓,我也不知道原來公寓都是秘密的刑場。
那晚我在曬衣場呆站了半晌,癡癡看著女大生嗚咽。我並不是同情她才留下來,我是想到那小我兩屆的高中學弟,曾經在新生球場那裡打過幾場球,平時補習下課後搭公車也遇過幾次,說起來也是會過著有女孩子和搖滾樂團點綴的大學生活的平凡男孩子,不過似乎還沒怎麼享受到,入學才幾個月就出車禍走了。
『據說是騎摩托車夜衝基隆哪。』在同學會提出這種話題的人往往都是留在補習班領鐘點的優等生,他們在學弟妹間似乎很受歡迎,某種程度上也算是會走動的小道消息,不過卻不怎麼受同年齡女孩子歡迎。
『他籃球在那一屆算很會打的吧?』
『好像鼓也打得不錯。』
『真可惜哪。』
半夜被自己室友拋棄、在屋頂用菸頭烙燒衣物的女大生要是自殺,被記者採訪的我如果能說『情傷的夜晚在頂樓哈菸解悶』,她會不會死得不那麼不值得?
『小傑啊小傑,真有你的。』站了半個多小時,我酒醒了也睏了,『管他女大生是要用小傑的球鞋摀住口鼻,還是用護踝勒住脖子,那都不關我的事了。』當時我這樣想。
下捷運後我步行到吉野家買了大份的豬丼、豆腐味噌湯和檸檬紅茶,吉野家店頭裡播放的濱崎步夏季單曲只讓我覺得十月底的台北盆地燠熱難耐,這種溫度濕度應該聽南方之星的<希望之轍>還比較爽朗。
「啊!你回來了!剛剛本來還想說叫你幫我帶一份海南雞飯回來……」阿凱陷在沙發裡噘著嘴說,眼前灑了幾本共筆,手中轉著一支黃色螢光筆。
「賣海南雞飯的今天沒開。」我掃視滿地上的蘇打餅乾屑和垃圾筒裡空無一物的冰淇淋筒說。
「啊?那我問小傑要不要叫麥當勞外送。」阿凱重新穿上藍白拖,將散落的餅乾屑集中在一塊兒。
「他沒有回南港?」我打開電視,從卡通轉到談話性節目、電影台,最後還是停在新聞台。
「PBL回報好像做不完,」阿凱從桌腳拿來一瓶雪碧,「看他傍晚回來後就一直翻大哈,還來我房間借POMD。哇,你看這個……」阿凱直指電視新聞,「社會上總是有變態呢。」阿凱灌了一大口雪碧。
「……欸,你知不知道我們對面住誰啊?」喝過一口檸檬紅茶後我才想到原來我一整個下午都沒喝什麼水。
「不是住一個上班族?看領帶好像是作汽車業務的。」阿凱不知從哪又抓出一包腰果。
「還有住其他人嗎?」我站起身到餐桌上拿自己的筷子。
「不知道。」阿凱把鼻子湊到我的豬丼,「我真的餓了,我叫小傑直接出去買。」
「你明明自己有機車。」我一個人坐在電視機前咕噥地配著小傑邊沖澡邊走音的<YMCA>扒飯吃。
結果那天晚上直到差五分十二點、母親從香港打電話來之前,我順利做完兩份腸胃科學的考古題,還順便用臉書聊天功能問了幾題我翻書後還不懂的題目。
「你過得好唔好?」我一直不明白,母親嫁到香港後的來電為何都只說廣東話?
「好忙阿。」幸好國中班上有好朋友會粵語,就陪我看了幾部港劇讓我熟練。
「還會去吉娜嗰邊食飯嗎?」
「會阿。」那忽然不像是我平常說話的聲音。
「感恩節後我跟你爸會回台北。」我不過感恩節,國中之後每年我都得查感恩節是十一月的第幾個禮拜幾。
「佢今年想待幾耐?」去年我繼父嚷著想去莫斯科過聖誕節,在台北待不到一個禮拜他們就飛走了。
「仲未決定,快接近再跟你講。」無論說與不說,言語都無法超越心思吧。
我聽見母親似是喝了口酒抑或是咽了口水。
「……我差唔多要瞓左。」我這是在放過我自己還是在逃避?
「早唞,保重阿。」
「媽早唞。」
像這樣虛應一應故事的對話,於母親而言是否為一種凌遲?對繼父呢?我以前不懂事,總以為悲觀任性就能帶來圓滿的光景,殊不知越是有缺陷的事物才越接近所謂美好的本質。
「小彬睡了?」我打開房門到冰箱拿了昨天喝剩的爽健美茶,看到阿凱還蜷在沙發上用筆電讀考古題。
「嗯阿。」阿凱把筆電放到一邊,「你要睡了?」
「差不多。」我把空瓶放到流理臺附近的資源回收塑膠袋。
「幹,你們都那麼早睡。」阿凱換了個姿勢。
「我們班打系壘的都還有留嗎?」開學已經一個多月,現在問這個話題是晚了。
「都還在阿,只是學長進醫院之後,嗯……,反正我們這屆要加油。」阿凱故意擠出雙下巴。
「小傑最近有沒有交新的?」我靠在沙發邊拉筋。
「不知道耶,沒問過。」阿凱好像不知道自己貼著螢幕看資料的時候會有鬥雞眼。
「好啦,真的要睡了。」我想趕快轉過身作個誇張的傻笑。
「晚安!」阿凱還真的一點也沒有把螢幕拿遠的打算,我暗自在心裡揣摩有鬥雞眼男友的樸實女高中生——那種連補習班物理課也幾乎不遲到的樸實女學生,雖然對物理一點興趣也沒有,不過練習題還是相當認真地完成、考試也能大致拿到基本分;並不是不在乎前途,不過樸實女學生還是花時間用各種顏色的原子筆寫交換日記給鬥雞眼男友,鬥雞眼男友或許也認真而笨拙地分享自己說出來都不好意思的夢想……但那樣的青春最終沒能將兩人帶到哪裡。然而也有人認為,樸實女學生追求的青春是不點破鬥雞眼秘密的悲哀戀情;鬥雞眼男友想像的純情是默許鬥雞眼事實的窒息情感。如果兩人都懷抱這樣的破滅,各自平凡地結婚生子,也在接近四十歲前遭逢失婚危機,還能毫不猶豫參加高中同學會,不著邊際地閒扯牙周病的話題嗎?
或許阿凱過的就是這樣的人生,沒有太多可以捨棄的東西。
「對了,我好像還沒告訴你,」阿凱突然放下筆電叫住我,「剛開學的時候我去申請補宿,前幾天補到了,所以我可能隔幾天會搬回學校。」
「小傑和小彬都知道嗎?」其實我並不喜歡公寓多出空房。
「他們都知道啦,」阿凱歪著頭,若有所思地收拾筆電和散亂的共筆,「還有,小傑說,他下個週末也準備要搬回家裡,好像是三下成績單太慘,被家裡唸了。」
「他也真辛苦。」不知道麥當勞女大生現在過得好不好?
「我是有先問過幾個系壘的學弟看他們要不要來住啦,應該禮拜三我們練球完之後我會帶幾個來看格局。」阿凱說完之後抿著嘴,無意義地彈指頭。
「可!反正你跟小傑約同一天搬,你請他開車把東西載去宿舍,你也不用那麼累,我跟小彬也可以幫你們把東西搬下去。」小彬急性子,要是有他在,很快就搬完了。
「他完全不會打包!」搬家的那天下午,小彬在阿凱的房間近乎歇斯底里地把所有歷年共筆、講義按照年級分放到不同的紙箱,阿凱還在小彬的指示下,跟小傑到家樂福拿空紙箱,「這種東西國考也不會讀到了吧,還留這個做什麼!」我將小彬棄置一旁的書本紙張統統放進黑色大塑膠袋裡。
「只會讀書,其他真的是什麼都不會!」小彬邊說邊俐落地把紙箱封起來。
「我先把紙箱搬到客廳。」就算我多附和什麼,對搬家這件事本身也沒有幫助。
「哇靠!」小彬衝到客廳,「你看這個!」我並不很想直視那過於刺耳的聲響,不過我看見小彬手裡抓著幾條童軍繩,繩子本身有幾處是燒焦的,「還沒完,你進來房間看!」
兩件褲檔燒焦的籃球褲和一雙有泛黃斑塊的髒籃球鞋無恥地被攤開在阿凱床邊的地板,籃球鞋裡面塞著兩雙顏色式樣不同的女用褲襪,我彷彿聽見小彬手中緊握的童軍繩正以慘叫代替指控,回過神來才知道那是路上孩童追逐的尖叫聲,而那讓公寓所在的巷子顯得有點歪斜。
「你在哪裡挖出這些東西的。」我默默地蹲在黑色大垃圾袋旁邊。
「我看阿凱書櫃最下層有一個紙箱,想說可能也是放以前的共筆,就拆開來看。」小彬指著那被粗魯扯開、印著乖乖餅乾圖樣的紙箱。
「……是不是先放回去比較好?」我悄聲說。
「嗯。」小彬露出失望的神情,「不過阿凱一臉呆相,竟然也有這種興趣。」
「這個嘛……」我看了看時鐘,「他們也差不多快回來了吧?」
「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怎麼可能。」我動手繼續搬運封箱好的書籍。
「真是變態啊!」我聽見小彬用力把紙箱踢進書櫃下層。
「我下去買個舒跑。」我急忙穿上黃綠配色的哈瓦士人字拖鞋,「今天實在太熱!」
一層又一層穿過昏暗的樓梯間,我從來不曾覺得住戶堆放的雜物如此讓人窒息,我無法克制自己不去思考,家家戶戶的雜物代表的是瞞騙棄置的秘密還是物質過剩的豐足?堆放雜物的人究竟想告訴誰這些事實?而我又能說給誰聽呢?
走到公寓一樓大門口才發現我匆忙中忘記帶錢,這讓我倏地冷靜下來。我感受到後背的汗浸濕了CELIO海軍藍條紋襯衫,被紫色廣告顏料弄髒過的蛋黃色百慕達短褲也沾到樓梯扶手的油污,前些日子在淡水老街買的嵌名腳繩也不知鬆落在哪——我噗哧一聲笑出來。
「你一個人在傻笑什麼阿?」小傑拿著幾個紙箱從巷口走來。
「想去買飲料,可是忘了帶錢,真蠢哪。」
「這樣啊。」小傑放下瓦楞紙箱,從口袋掏出幾張紙鈔,「你看要去哪裡買什麼都好,反正買四杯吧。」
「你確定?」小傑沒有回答。
而我後來也不知道我買回來的合不合他口味。
那晚公寓只住著我,一個人在黑暗中打開小彬電腦裡的隱藏資料夾,連續播放總長度超過兩百四十分鐘的高中女生大小便的偷拍影片,我把音量開到最大,每當喇叭唱出沖水聲,我就喝一口無糖綠茶。直到四大杯全被我喝完之前,我都忍著沒去上廁所。
後來阿凱介紹的兩個系壘學弟並沒有搬進來。阿凱和小傑則是透過房東告訴我,他們會以轉帳負擔應繳的房租,我因此沒向他們要回公寓鑰匙。至於小彬,我們還住在一塊兒,卻許久不曾交談了。
「嘿,你媽他們是不是快回台北啦?」新陳代謝科考試前的週末晚上我接到來自吉娜姐的提醒,「星期四吃飯的時候忘記告訴你,今年還是像往年一樣,我請人把你們公館那邊的房子打掃一下,錢我再跟你媽拿就好。」
「不了,」我喝了口自己做的梅子檸檬水,「今年我想自己掃。」
「這種事我來處理就好,你不是很忙?」吉娜姐的聲音似是在床上磨蹭。
「反正隔幾天我自己去掃,周四見。」這幾年我與人談話總避著提到「回家」,儘管自知是無謂的努力,卻始終不承認自己早已無處可逃。
十年前父親過世沒幾個月,母親便決定飛過黑水溝改嫁。當時我以為再沒有什麼可以失去,執拗要母親留在台北,沒想到最終我竟連「家」都無力追討,只得掛失——這個月以來和小彬兩人蟄居的無聲公寓讓我想起那段記憶,一直到後來吉娜表姐收留我之前,我沒有一個可以說「我回來了」的地方,狀況和現在的確雷同。我懊悔那硬是將自己逼得別無選擇的我,如今我想放過自己,而我必須回到一切的起點。
週一考完新陳代謝科的晚上,我請小傑陪我打掃公館的房子,「房間都交給我就好,客廳就麻煩你。」我想測試我自己能否正視被房門掩沒的記憶。
首先是母親的房間。過時的毛呢大衣飄來股霉味,滿是灰塵的香水瓶身還搖得出幾滴,彈簧床上的記憶枕好似說明它的主人長久以來睡不沉。我在母親的梳妝鏡前坐下,查看我和記憶中的母親有幾分神似,假若撲粉遮瑕,繼父會不會誤認我為母親?母親會不會對我多一分憐惜?
我拉開玫瑰圖樣的象牙白窗簾,光線昏暗,狹窄的防火巷竟空無一物,好似大夥兒相約遠遊。我擰乾抹布,雙膝跪地,連線頭都不放過地隨木頭地板花紋潮來又潮往。
「嘿,你竟然會有這個!」這幾年室友一場,我當然知道小傑愛聽張國榮還愛唱那首<拒絕再玩>,「跨越97演唱會!我最喜歡這場,你知道的!」他在客廳大聲叫嚷。
「我都忘了,去年我從香港帶回來的,本來要給你當生日禮物,後來我自己捨不得。」我到陽台換水,「你看到了就是你的,哈哈!」
「我把它放到DVD裡面播,」小傑興奮地拿出光碟,「讓周圍有點聲音也好。」
大約是唱到〈怪你過份美麗〉的時候,我提著橘色塑膠水桶走進自己的房間。衣櫃裡連一件合身的衣服也沒有,書桌下堆放的雜誌或色情漫畫書頁幾多泛黃,床底下的單簧管也沒有備用簧片可以振出聲音。我悄悄關上房門,把全身的衣物脫光,用潮悶異常的棉被包覆自己,側躺著翻看襁褓時我和母親的合照。
幾分鐘後我放回相本,以有點俯瞰的角度彎腰,擦亮我曾住過幾年的房間。
「客廳地板還有茶几什麼的都擦乾淨了,」小傑還提了一大包食物,「我剛剛下樓到路上去買了鹽酥雞和綜合果汁,你把髒水倒掉,我們一起看完DVD,也快到最後一首了。」
〈追〉。
「最近有沒有新對象?」,我啜吸著綜合果汁。
「我累了,想休息一陣子。」小傑連吃了幾個雞心。
「以前沒看你這樣過。」我叉了百頁豆腐和九層塔。
「你也不是不懂。」小傑斜過頭看著我。
「麥當勞女大生搬去哪了?」我從小傑帶回來的便利商店塑膠袋拿出兩罐啤酒。
「這要問阿凱囉。」小傑把綜合果汁喝光。
「她搬走前有沒有跟你說什麼?」我遞了一罐啤酒給小傑。
「她說你是好人。」小傑咕嚕咕嚕地喝了一大口。
『我希望你們能夠永遠記住我。』張國榮在演唱最後一段副歌前這麼說,我確實聽見了。
評審評論
- 王:這篇是一篇很棒的小說,讀了就會知道那就是變態的大集合,大家都在亂搞,就是跟性有關。這是一個內容跟篇名最符合的一篇作品,一開始我就聯想到王聰海一個小說「壞掉的人」,在描寫這個世界正在崩毀,每處都非常的腐敗噁心。這樣的小說對於一般的人來說是有衝擊性的,這是一個很棒的部份。但是這部份的小說處於噁爛中卻是非常純真,這其實是用純真的外衣來包裹,每個人心裡都還保有一些純真的樣貌並沒有被噁爛所摧毀。另外他用大量的對話,文筆也非常親民,使整個故事看起來非常有現代性,是很好的作品。
- 高:這是一篇結尾很漂亮的小說,這個小說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在於他把變態寫得非常日常化,這些主人翁並沒有覺得自己很變態,而是坦承的表示這就是此時此刻的我。對於小說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張力的作品。
- 羅:自古以來有很多描寫變態的作品,我回過頭去想用這個變態的主題是要來處理什麼。當中他母親後來嫁去香港而用廣東話來和兒子對話,是我比較有興趣的部份。
評選結果
編/王/高/羅/計/名
03/06/03/00/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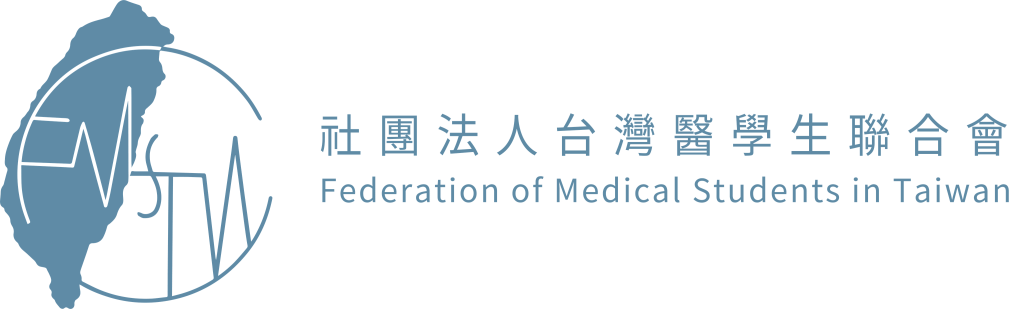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