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屆散文組首獎]書呆子《一生追尋的天空》
高將軍正要告訴我他一生追尋的天空是什麼樣子,主治醫師卻來了。
「今天還要來做嗎?」高將軍問。
「你腦壓太高了,要每天抽脊髓液把壓力減下來。」
「一定?」高將軍呻吟了一下,把頭埋進枕頭裡,用那被悶住的聲音咕噥著:「一定要每天嗎?」
「一定。」
「你們都說抽完會比較好,我的頭還是一樣痛,還是一樣狂吐。」悶住的聲音繼續抱怨著。
「我們是擔心你的眼睛。」
枕頭拿開,高將軍嘆了一口氣:「我的眼睛會好嗎?」
「我們不能保證。但眼科說,只要繼續控制腦壓,不是沒有機會。」
「我現在白天晚上都分不清楚,看出去都是模糊一片。」高將軍坐了起來,在桌上摸到了水杯,嘴巴卻一直湊不到吸管,兩頰被扎了好幾次。
沉默了一會兒,高將軍以一種乾澀的聲音問:「下午來做嗎?」
「等一下。」
又是一陣沉默。
「好吧。」病人妥協了。
主治醫師穿著白袍冷冷地離開。
高將軍一個人躺在床上,隆起的顴骨,凹陷的臉頰,頭髮稀疏而膚色蠟黃。
一旁放著他的照片,帶著墨鏡穿亮橘色的飛行衣站在F-16戰機旁,好威風,好帥氣!
談到高將軍的眼睛,我便想起霍豐華,我們都叫他阿華。半年前我在燒燙傷中心見習時,遇見了他。全身98%燙傷,學長說,就算他能夠幸運的活下來,將來也注定是個瞎子。直到現在,我還是有空便去病房看看他。
第一次翻開他的病歷,裡面一張張貼著他剛被送來時的照片。全身黃一塊,白一塊,一片爛紅,滿是焦痂,水泡四起,像是被發瘋暴怒的畢卡索亂抹一氣,糊里糊塗,看不清楚。聽說他以前是地下錢莊負責討債的,被人家丟了一顆土炸彈,炸成這個樣子。我看著阿華照片中支離破碎到幾乎無法辨認的雕龍刺鳳,試圖想像曾經的他,是怎樣生活在社會不見天日的皺褶之中。真如媒體描繪的那樣,在幽森的陋巷中穿著沾滿腥泥的皮靴恣意踢打?在陰暗的敗屋中燒紅吱吱作響的刑具?爛醉在暗藏春色的按摩店中?現在的他,被包紮得那麼雪白而純潔。
這裡,像阿華一樣的人太多了。空氣中隱隱透著一股陳悶潮濕的焦臭味,像是無法無天的死小孩將數十支沖天炮瞄準公廁炸了個天女散花所瀰漫出來的味道。他們痛苦的不停扭動身軀,發出如蠶房中嚼食桑葉的細微聲響,沙沙沙沙的啃入你的耳朵,啃入你的聽道,啃咬著你的腦子。冷不防某一床發出一聲哀號,彷彿在邪雲掩月的深夜偷越陋巷不慎踩到的惡貓,那樣的詭譎,那樣的淒厲。
只有阿華,總是一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裏,無聲無息。
一直到那濕冷的掌心緊緊握住我放在床緣的手,我才從燒燙傷中心跌回高將軍的哀號聲中。此刻的他,赤裸地蜷縮於床緣,無助脆弱如初生的嬰兒。床看起來好大,他人好小。背上布滿新舊各色的針孔,暗紫的、淡紫的、褐紅的、淺紅的……,周圍的肌膚瘀青浮腫,一根細長的針穿刺其中,微黃澄清的液體泊泊地流了出來,一如那天高將軍告訴我的天空。
那天,同樣也是做完脊髓穿刺。被規定要靜躺六小時,百無聊賴的高將軍開始談起他驚悚的航行。那時,他們誤入暴風雨之中,像是萬里的黑潮猛然地掀起捲來,將機身吞入無邊無際的渾沌之中,雷電的蒼白毒舌恣肆的四處舔舐,亂雲化作的巨獸怒瞪著血眼撞來,儀錶板的指針發瘋似的來回跑竄,馬達歇斯底里的尖叫著、嘶吼著,機身開始顫抖、痙攣、癲癇。他們隨時都會墜落,荒野的亂山會化作撒旦的巨拳將一切揍得粉身碎骨。一股奇寒凍徹了五臟六腑,沿著脊髓直竄入腦中,彷彿全身都散作細小的冰粒,那麼微不足道、那麼無助的懸浮著。此時,在上下左右東西南北此時被揉轉扭曲得無以復加的此時,也就只能緊緊握住如待宰的驚豬般奮力掙扎的方向盤,航向你相信北極星的所在。
驀地,飛機彈出了雲塚,晴空劈面壓下,將腳底的風暴轉瞬推遠。
漸漸的,微風將流雲梳開,世界只剩下天與海以及靜止於其間如蜉蝣般短暫渺小的機身,晨曦在波紋間追逐嬉戲,由東至西漸漸的織就一片繁麗璀璨的星海。天地倒轉過來,他們便沉浸在清澈金黃的永恆之中。
後來,在那劇痛之後的休養中,高將軍還告訴我許多天空的故事:熱帶雨林蠅巨過掌的天空,西藏粹藍得直貼胸膛的天空,北極極光流竄的天空,大漠狂沙掀舞的天空。高將軍常說,等他眼睛好了,要帶我去見識見識。
每次聽他講起,我便想起曾經,我和士凱也共同懷抱著偉大的夢想。我們約定有朝一日要跨出這蕞爾小島,像Georgia O’Keeffe,帶著畫筆流浪在荒涼的奇境。那樣的歲月裡,我們會在放學的時候,爬入美術老師忘了上鎖的氣窗,偷他那昂貴的進口顏料,然後忘記說好要練習的水彩,把對方的臉塗成張飛、曹操。偶爾也將Raphael的石膏像走私回家,在午夜的肚臍眼兒上點一盞小燈,暗自擔心素描的沙沙聲會把全鎮的人都吵醒。或是教室布置時在牆面上黏一隻性感而修長的絲襪假腿,讓路經的女老師都為之氣結。有時我們也狂想用古老的砲台將夕陽轟下,一路的碎石搔弄得鏽歪的單車花枝亂顫地吱吱直笑。我們在峭壁上磚石零落的牆緣倒立,血液漲滿了腦袋,將萬籟摒去,只有心跳是那麼的清晰朗澈。感覺雙腳正踏著遼闊的天空,將世界整個舉起。
是否也有一個曾經美好的過去?我望著阿華時常這樣想,尤其當那漂亮的女孩子來看他時。她剛開始每天都來,常常頭髮有些凌亂,雙眼有些浮腫、紅紅的。日子久了,阿華一直沒有醒過來。漸漸的,女孩子來的次數就少了,開始也會穿一些亮麗的洋裝,頭髮也梳得烏黑秀亮。最後一次看到那女孩子時,耳上別了一顆心型的粉鑽,看起來真是活潑俏麗。我親眼看到,那女孩離開時在門口停了一停,然後頭也不回地離去。不過穿著褪色碎花上衣的婆婆倒是固定隔一兩天就會來,從他們遙遠的村子,中間要轉搭好幾次車,通常清晨出發,都要過了中午才到醫院,然後婆婆就一直坐在外面走廊的椅子上,等。等到下午五點的會客時間,進來看一看他,然後在深沉的夜色中搭車回去。不過婆婆已經不再來了,聽說,是沒有辦法再來了……
除此之外,就不曾有其他人來探望過。
有時,高將軍也會講起他家人的往事:那是在抗戰時期的某日,他爹和他叔叔瞞著兩人的娘到江邊去放風箏,褪色的大紅風箏在朗潤的的藍天中躍動著,像是一顆無憂無慮的心。驀地警報四起,像是一把長刀狠狠地劃破了長空的平靜。小孩兒貪玩,還撥弄了一會兒風箏才不甘不願的拾掇了。霎時間,頭頂掠過一架戰機,幾點光亮驟然落下,只聽得霹剎轟隆數聲巨響緊隨著一陣天翻地覆,彷彿全城是坐落在厄運女神的地毯上給狠命一抖,家家戶戶便此起彼落的跳動著。緊隨著爆炸完的短暫平靜,濃煙的巨人四處站起,凌亂模糊的臉痛苦而扭曲,搖搖晃晃地翻身跌落。他爹拉著他叔叔沒命的奔跑,他叔叔不甘願的抓著那褪色的風箏,磚瓦、家具、碎石如暴雨般沿途砸落,正經過家門時,一陣怪風忽地將風箏攫走,他叔叔鬆手便欲追去,說時遲那時快,一片頹牆劈面壓下。對面的高樓像是一顆缺牙滑稽而歉疚的佇立著,斜陽的淚眼將原本被遮蔽的遠天染得好紅,好紅……
一遍又一遍的,在夜晚昏黃的燈光下,他爹抱著他坐在膝上告訴他:「孩子,你要勇敢的飛上去,飛得高高的!不要像你爹!摔死總比炸死的好!」
不過,高將軍再也沒有提起他一生追尋的的天空。或許他是忘了,或許在萬針穿刺的凌遲中,他已毫無興致。
高將軍的腦壓還是一樣的高。
甚至,開始莫名其妙的發燒起來。
奇瑰的故事漸漸被胡言亂語所取代。偶爾清醒的時候,他只是愣愣地問:「今天的天空怎麼樣?」
常常我轉頭望了望,冷冷玻璃窗外幢幢的高樓,高低錯落的將遙遠的天空切割成隨時將支解的幾縫空間,我也不確定現在的天空究竟是藍色,是灰色,還是沒有顏色……
在沉默中,我注視著他的眼睛:深邃的瞳仁,映射著周圍的數點幽光,彷若正管窺一浩瀚的宇宙,無數的星辰在純黑的夜空中,不斷的旋轉著。我渺小的身影也倒映在其中,跟著旋,旋,旋,旋入那遙遠的未知之中。
我永遠想不到的是,在另一間病房,奇蹟真的發生了。
阿華漸漸地可以自己坐起來吃東西,頭上的繃帶拆開了,連視力都以驚人的速度恢復著。
那天我去看他時,他木著一張臉,彷彿連眨個眼睛,抑或是露出一抹酒窩,都會撕裂那薄如蟬翼的新皮。手腳都紮著層層的繃帶。然後他吃力的扳開右手的手指,顫抖著握緊了湯匙,舀了一口粥,晃不咧爹的往唇邊送,途中猛然抽了一下,數滴飯糜都灑在了衣襟上,到嘴中時已所剩無幾了。然後他就這麼舀粥,灑落,再舀,再灑……
過了一會兒,阿華注意到我的視線,他轉過頭來對我靦腆的笑了一笑。
我這才細細的看清了他的容顏,是一張多麼純樸溫和的臉啊!實在很難想像那猙獰的過去。
常常,看著阿華凝望著拉著厚重窗簾的窗戶,我不禁想:有多久,沒有好好地看過天空了呢?自從士凱家裡出了事,毫無預警的搬家失聯。我的生活也失去了重心,渾渾噩噩的在考卷與書堆中渡過,也就這麼上了大學,進了醫院。每天早晨,掀開棉被,一頭便栽進昏暗的浴室裡胡亂刷洗。俯首看著手錶匆匆趕路,隨著捷運的車廂駛入城市地底深處的盲腸,慌忙四顧的在車陣中穿梭。好不容易進到了醫院,在到處飛舞的病歷堆之中失去方向,直到夜深時分,然後垂著頭,拱著背,斜靠在沙發上想說下看個新聞卻不小心睡著了。
阿華要出院的那天,窗外的天,好藍。
一如後來,我意外收到David Florimbi的Going and Coming系列明信片。那是士凱從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寄給我的,Georgia O’Keeffe曾經讀過的學校。不同於一般畫作中被當作微不足道的背景,David Florimbi的天空是一種毫不遲疑的純粹的滿漲欲瀉的藍,沉靜中卻蘊透著一觸即發的力量,在畫布中理直氣壯地逼壓著無邊曠野。一切的草木山川,都縮移變形退幾至邊緣,彷若沙漏中的細瑣,轉瞬即逝。
我看著阿華,不知道為什麼,我忽然想起The Shawshank Redemption中的老Brooks,在獄中待了五十年後假釋,終於能像那鳥兒自由的翱翔於藍天之下時,他才發現,一切都已經變了,路上到處奔竄著他童年罕見汽車,矮小的平房變成幢幢的高樓,……
阿華告訴我:他想改行做計程車司機。不想幹活的時候,就把車子拋在堤防邊,躺在沙灘上,看海,看天。
那時候,我並不知道,高將軍正因為病情的急速惡化,和他那鷹隼般銳利而明澈的雙眼,一起被推入了加護病房……
評審評論
柯:寫得非常好,大概至少寫了三個人生吧,等於說在一個人生很困頓的時候去回想這些人是什麼樣狀況的,從這邊又連到了一個高中同學。高將軍的天空、阿華臉上的傷、朋友的明信片、高中的藝術作品,把顏色狀態情感全部連在一起,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可以做的方法,這個對位是非常令人激賞的超越。形象非常精確,以畫作來比喻人生的各種狀態各種情感,寫得非常好。
鍾:這篇的作者真的很厲害,這麼多線竟然有辦法連在一起,那個記錄片的手法、悲哀的那種過程以及他自己青春理想的扣合。高將軍天空的描寫真的是太精采,那文字真的是飛翔的,令人讚嘆。
李:描述天空或身體的感知,都抓得很到位,可以讓三條線沒有破綻的織綴在一起,雖然一開始看起來是沒有什麼關係,但運用天空的意象把他們不同的生命故事串在一起,我覺得也是個很成熟的寫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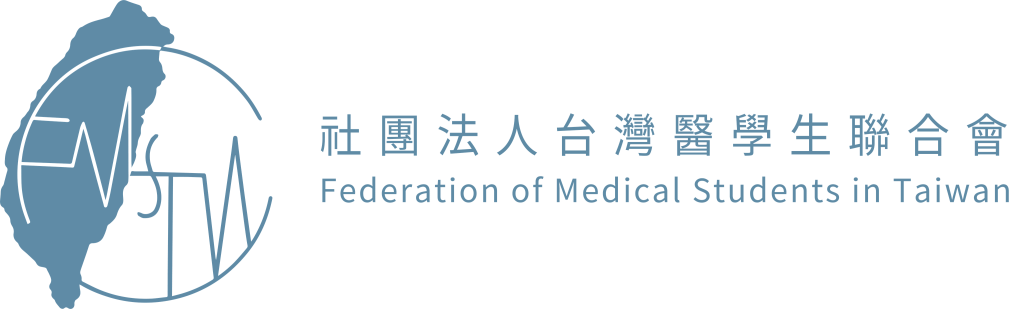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