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小說組佳作]能泗《放手》
醒來的時候,還沒接受光線的刺激,最先感受到的,只有那劇烈的頭疼,疼得我幾乎想滿地打滾,可四肢百骸卻空蕩蕩的使不出半點力氣。
我只好滿臉扭曲的躺著,意識不斷的拉遠又拉近,本能的想紓解這疼痛,可大腦的運作基本是零。
視力還很模糊,眼前盡是白茫茫一片,分不清是光還是天花板。
也許有一段時間又暈過去了吧,我不確定,這種半夢半醒的浮沉感讓我很難分辨現實與夢境。
不知道又過去了多久時間,手背傳來的冰涼觸感讓我下意識縮了一縮,我才發現自己終於稍稍脫離了先前的渾沌,而且有了控制軀體的實感,就像是靈魂和身體總算接合那樣。
這時候甚麼想法也沒有,腦中一片空白,只是呆滯地盯著天花板。
這樣的安逸沒有維持太久,我忽然感到心臟用力一擰,接著一股涼意就竄了上來,沒來由的恐懼驚得我反射就往旁一個打滾跳了起來。
沒有想到,還處於伸展狀態的肌肉禁不起這下劇烈刺激,腰部一下傳來劇痛,躍起的同時我也慘叫一聲,重重的摔倒在地。
內心的警鈴仍敲的作響,我立刻掙扎著翻了起來,警戒的向四周望去。
這一看去,我登時懵了。
眼前是一個……恩,我不能肯定,也許是房間?它不大,約莫公寓客廳大小。我並不認得這裡,但這不值得大驚小怪,以我的心理素質,就算醒來發現自己躺在棺材裡都不會這麼驚訝。
可這個「普通」的房間,四周除了基本該有的四面白牆外,甚麼都沒有。
真的甚麼都沒有,沒有傢俱,沒有擺設,全是一片的白茫,襯的好不寬闊。
乍看之下,我只隱隱覺得有甚麼不合邏輯。但下一刻,我弄清狀況後,冷汗一下全冒了出來。
沒有門,這四堵牆沒有一面有開口!
強烈的恐懼感剎那間又翻騰出來,我的心臟狂跳不止。
為甚麼我會躺在這裡?……在這之前我在哪裡?做些甚麼?
我下意識地就搜索起腦中的記憶,奇怪的是,最近的事我竟然一點印象也沒有!我明白我是誰、我的父母,還有那群狐群狗黨們,獨獨缺少那一段最近的時間。
沒有甚麼比這時候失憶更加可怕,我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眼前怪異的景象更是搧風點火,阻礙我的思路,我忽然感到十分不現實。
不管如何,我得先試著出去,出去之後其他都好說。
我伸出手貼上了牆,冰涼且堅硬的觸感立即從掌心傳回,曲起指節敲了敲,響音小的幾乎聽不見。我立刻知道,這是實打實的磚牆,除此之外,厚度肯定不一般。
我還是每道牆都拍了遍,全都失望,沒有一面是保麗龍。
我不死心地抬起頭,看了看天花板,往上用力躍起試著推了幾下。紋風不動,也是水泥澆的。
也就是說,這不是夢,太逼真了。我大概也不是意外進來,而是有人故意為之。
我轉往牆壁抬手猛捶,順便用盡吃奶的力氣大叫大吼。
就算水泥牆再厚,只要不加隔音泡棉,聲響總是能傳出去。雖然我不知道這房間的位置,但如果有人經過,被怪聲吸引一探究竟,抑或是隔壁鄰居嫌吵打電話報警,那我都有逃生的機會。
就這樣拚命叫喊了十來分鐘,喊到聲音都啞了,口乾舌燥到極限,才連連咳嗽打住。
仔細想想,對方擺明了要把我困死,這裡或許根本就是兇手的地下室,再怎麼傳也不過是對方的飯後娛樂。說不定還有個隱藏式攝影機呢,正愉快的觀察我的種種反應,我反胃的想起了那些美式驚悚片。
這種時候再折騰也沒用,我逼自己冷靜下來,一條一條地把醒來之後的所見所聞都梳理一遍。手邊沒有任何紙筆,我只能最大限度的活動我那所剩不多的腦細胞。
首先是失憶,這是我最不能理解的部份,畢竟不是狗血劇情節,想讓一個人失憶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事,而且還要指定某段消失,那幾乎是天方夜譚。
如果這不是對方本來計畫的一部份,而是一個意外呢?
我忽然想起以前常發生酒喝多了,早上醒來前晚的事一個也記不得的狀況。
還有一個可能,我想到方才的頭疼欲裂。也許是被誰狠狠敲暈了,然後基於某種原因把我扔到這兒來。
我下意識地摸了摸頭,猛然發現沒有腫包,也沒感覺到傷口。
這就奇怪了,要怎麼敲才能把人打暈又不出現傷口?
記得似乎曾看過報導,有一些迷幻藥會讓人昏沉,而且隔天起來完全沒有了用藥後的記憶。
如果是這樣,副作用可能就是頭疼。
那麼到底是誰,和我有這般深仇大恨?
我的腦海中瞬間浮現出密室殺人案件,但立刻就覺得這想法錯誤的離譜,密室好歹也是有門的,只是被從內反鎖罷了。和我的情形完全不同,這裡可是真正意義上的密閉。
我手邊沒有工具,靠自己肯定出不去,如果也沒人發現我在這,搞不好一輩子就得待在這鬼地方。
不,我大概也沒機會老死,先別說食物的問題,光是空氣不流通這件事,我要不了多久就會先缺氧而死。
這是甚麼奇怪的死法,在一個密閉空間窒息而死,我幾乎可以想像最後幾天的痛苦掙扎。
在那之前我肯定要留下血書,就寫「死不瞑目」好了,然後變成魂魄後趕緊穿過牆,找那傢伙算帳。
聽起來還不賴,我一點也笑不出來。
我才活了多少年,甚麼也沒享受到,為甚麼現在就要死?為甚麼非得是我?
腦子現在正分成兩邊進行,一邊是悲觀的叫囂著出不去出不去,另一邊則是激勵著自己不要放棄,絕對有辦法的。
我就這麼在衝突中苦苦思索,腦中忽然靈光一閃。
我是怎麼進來的?
首先已經先排除掉噩夢的可能性,所以,在這裡所發生的事都應該要能最低限度的符合邏輯。那麼,要把我放進來而又是完全密閉的狀況,是不存在的。
但現在它發生了,說明了一定有甚麼辦法,我試著推敲幾種可能:
第一,房子建好後打個洞,把我扔進來後再補回去。
第二,先把我扔在這,再往我周圍蓋牆,等於是先抓獵物才造籠子。
老實講,第二個我覺得完全不可能,除了太麻煩之外,這樣太引人注目,更何況建一個房子不是一兩天就能完成。想要趕工,工人就要請多,到時人多嘴雜,把一個活人關在房子這等怪事肯定會傳出去。
不對,要是工人完全不曉得有個人在裡面呢?等房子快蓋好時再偷偷把我扔進去不就好了,神不知鬼不覺。
想到工人,我盯著刷了白漆的牆,忽然有種道不清的怪異感。一時沒能想明白,我沒再理會,轉而思考第一個可能。
如果補回去,那應該會有痕跡,我趕忙走向一面牆,有次序的一個直排慢慢敲下來,到底了再換下一排。
一面牆一面牆摸了快幾十分鐘,不斷重複的動作十分消耗我的耐性,我幾次忍不住想加快速度,都壓了下來。畢竟這攸關生死,要是那工人偷懶只是塞個報紙或保麗龍進洞,外面再糊一層水泥,那我也許還有出去的希望。
摸完第一圈時,雙腿都有些隱隱發酸,我咬了咬牙,還是決定再重頭來一圈。這次更加仔細,一小塊一小塊密度極高的搜索,雖然我明知若要容納一個人進來,那洞絕對小不了。但人就是這樣,有了希望就會緊緊抓住不放,因為要是放了,你就會感覺到比前次更深的絕望。
我又走了第三遍、第四遍,天花板也巡了一圈,可這牆面敲著都實心,而且別說痕跡了,一點凹凸不平都沒有,技術非常好,平滑的渾然天成。
認真工作也是會害死人的啊!
我腳酸得要命,累得背靠牆坐了下來,開始猜測兇手的可能。閉上眼,那些平常看不順眼的上司和同事的臉不斷在我眼前閃過。
給你們揍一頓就是了,有必要這樣整我嗎?我忍不住怒罵,內心卻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到頭來我還是像個將死之人,阻止不了回憶走馬而過。
說沒有遺憾是騙人的,因為人生總是有很多不得已和妥協。其實和大多數人比起來,我已經過的很不錯了,可就是有那丁點的遺憾,老讓我掛在心中。平常時候,是不能說的秘密,如今又隱約翻了出來。
漫無目的地想著想著,忽然有點想睡,也許是今天遇到的狀況太過刺激,我眼皮搭了幾搭,居然就毫無防備的睡著了。
再醒過來時,不知道是不是睡了一覺,我神清氣爽的很,一掃昨天的悲觀。疲勞和口乾舌燥也都消失無蹤,我站起來走了幾圈,把各處都觀察了遍。
這裡一定還有值得注意的地方,我看了看四周,一逕的白漆。雖然單調,但我很感謝不是藍色綠色,否則盯上幾天一定渾身不舒服。
又看了幾眼,我忽然醒悟,這會滿室光亮,但沒有燈沒有太陽,光打哪來?
昨天已經確認過沒有任何空隙,不可能透光。假使是別的東西發亮,我低頭看自己的影子,想循光的來向。
沒有想到,我的腳下竟沒有任何陰影!我目瞪口呆的抬腳動了幾動,腳下果真甚麼也沒有,往旁邊看看,牆角也沒有淡淡的影子。
因為水泥地是灰色,再加上從來沒有注意去看,的確不容易發現這回事。
這真神奇,我知道來自不同方向的光源可以造成多條陰影,但不曉得有沒有讓陰影消失的方法。
高中物理早就遺忘多時,我忍不住後悔當初幹嘛不多念一點。現下實在是參不透其中的奧秘,我又想了半天,突然有種奇妙的想法。
如果能活著出去,這絕對會是我人生中最值得炫耀的經歷之一。
但前提還是要能出去,我拋開這個,光的問題看來是找不到合理的解釋了,不如再往其他方向想想。
這一天我積極的走來走去,對自己提出了一大堆問題,沒有一個回答得出來。為了節省體力,我不敢運動過大,大吼也只吼了幾句意思意思。
這一天也就這樣過去。之後的幾天,我還十分活力的想嘗試新東西,提出新看法,有的能驗證、有的不能,能驗證的看法基本都是錯的。
再接著十幾日,甚麼新發現也沒有後,我的心態逐漸改變。除了固定的吼上幾聲,我連動都懶得動,寧願坐在那兒發呆。
就像是一隻不斷接受試誤學習的猴子,當知道按這個鈕一點效果也沒有時,牠絕對不會再碰那個鈕。
我幾乎沒有時間的概念,房子內的光也不會有亮暗的差別。生理時鐘卻還是正常運作著,把我送入夢鄉,再準時把我喚醒,繼續面對那空蕩蕩的房子。
為甚麼能撐這麼久?我也不曉得,只知道一天下來的疲憊與飢餓都會在睡一覺後徹底不見。初時還覺得天無絕人之路,高興的探討這件奇妙的事,可次數一多就習慣的接受了,甚至覺得有些可怕。
這樣的日子不斷重複,就在我因為枯燥乏味的生活而幾近崩潰時,發生了一件事。
那天我像往常一樣,機械的調了個舒服的姿勢等著入睡。閉上雙眼,腦中忽然響起了某個旋律,我一時想不起來,而且也有點睏了。但那旋律實在太熟悉,我禁不住也哼了起來,哼著哼著迷迷糊糊的睡去。
醒來後我立刻回想那段旋律,倒是記得怎麼哼,可是想不起來曲名。我打算繼續糾結在這件事上,手往旁一撐,卻被突起的硬物給戳了一下。
那一下疼的我立刻抬起手,定睛一看竟是一顆石塊。我不由得好奇起來,掃了一眼才發現不知何時,我靠著的那面牆多了個裂縫,離我不遠,大約一截小臂的距離。
裂縫不大,但有些深度,形狀有點像扁扁的三角錐。小石塊就是從這掉出來的,除了我壓到的那塊,地上還有許多散落著,不過有些還是塞在這裂縫中,好像有人砸了牆卻又不清乾淨。我伸手撥了撥裂縫,果然嘩喇喇幾聲又翻了些石塊下來。
太好了!我內心一陣狂喜,許久不見的情緒波動讓我眼淚差點掉了出來。
我快速的翻動著石塊,直把裂縫給挖成了個小裂洞,卻在下一刻忽然碰到了奇怪的東西。
那是在裂洞中心,我正扒拉著一個大石塊時,指尖卻傳來柔軟的觸感。我以為是幻覺,沒怎麼在意。好容易把石塊清下來後,一隻手就出現在我面前。
它剛好就擋在裂洞最深處,整隻手掌垂在那兒,手背正對著我。手腕以後的部分全埋在牆裡,我停了下來,有點不知所措。
第一個反應是有人把屍體埋在牆裡,我猶豫了一下,撿起一個小石塊朝那手扔去。又等一會,見那手確實不動,才大著膽子伸頭靠近。
那是隻右手,指節分明,只比我的手小不了多少,應該不是女人的手。不是一般屍體的慘白色,這只手讓人感覺十分鮮活,我隔著袖子戳了手背幾下,頗有彈性,居然不會凹陷。
這代表甚麼?這人剛死沒多久?還是……
我有點緊張地對著牆壁大吼「你還活著嗎?還活著就發點聲音!」
沒有動靜,這麼悶著,大概早就死了。我想了想決定繼續挖,先把它挖出來看看。能撥的石塊都撥掉了,我撿起地上較大的石塊避開那手就往裡砸。這一砸,手中的石塊竟應聲碎裂,脆弱的跟甚麼一樣。我捏了捏還殘留在手中的塊,依舊相當堅硬,可往這石壁一比就成豆腐渣。
又換了幾個石塊,全都敲成了粉,我改用手往壁裡摳挖,忙活一陣,連個屑都沒下來。
看來這意思是能挖的一碰就掉,不能動的部分就連一小片皮都不讓挖。
我一下洩了氣,失落至極,憑空多出裂縫的喜悅已不見。指尖傳來疼痛,我低頭一看才發現用力過猛,指甲都裂了。
那手還好端端的卡著,我轉念一想脫下上衣,包住它就試著往外拉。怕它被我扯斷,我不敢下死力,像拔河那樣一點一點的往外拉,那手紋絲不動,連一絲鬆動都沒有。
我鬆開手,檢查了一下衣服,沒有屍液,於是又穿了回去,回頭來研究這隻手。說實話,這手插在牆上還挺藝術的,頗有後現代主義的味道在。
指尖修長,指甲修得十分乾淨,看的出來這主人頗愛整潔。我將這隻手稍微往上扳,手掌還挺紅潤的,一點沒有死亡的氣味在。
這非常奇怪,但我在這些日子的折騰下早就麻痺,懶得去討論合理性的存在。反正也得不出結論,最主要是,我感覺到這裡似乎存在著某些規則,就像是情境式單機遊戲,要觸發了某部分才會出現下一個事件。既然如此,那麼我該探討的不是那些怪異的景象,而是需要觸發甚麼東西。
那一整天我都對著那隻手哼歌,我唯一能想到和前幾日不同的動作只有哼歌這件事。
隔天一起來我立刻看向那個洞,手還在,洞也沒變化。我並不是很氣餒,同樣一招怎麼可能不停使用。
一定是別的甚麼,我猜測和那旋律有關,可是任憑我想破頭都想不起我究竟在哪裡聽到的,還有關於這旋律進一步的資料。
既然如此,我盯著那手開始一首歌一首歌連著唱,亂槍打鳥總是會中的。我會的歌本來就不多,沒一會就唱完了,只好搜索枯腸,不記得歌詞的就哼幾下調調。
輪著唱了幾遍,唱到連自己都很無趣了,之前那種無事可做的痛苦陰影又浮了出來。
我不曉得魯賓遜漂流到荒島後的幾十天有沒有像我一樣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孤寂和無趣。我要能活多久,就得待在這多久,就另一種意義而言,這是最完美的無期徒刑。
不是只有今天才想到,這十幾日來每天都想,想到每一次的睜眼都祈禱著能看到別的景色。
反正也無事可做,我坐到手的對面,距離極近,有那麼一個恍神我以為看到它朝我的脖子掐過來。事實是我沒有閃,而它也沒有動,我卻感到一絲惋惜。
「你好。」
我鄭重的向它介紹了自己,包括我的名字、住址、喜好與嗜好,考量到它的狀況,我還沒有無聊到問它問題。
不用說,這畫面真是可笑至極。但我現在除了可笑外,也奇妙的感到心裡舒服很多。
我滔滔不絕的說完了屁話表面話後,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沉默了一會,我想了想,來說個故事好了。
「我有一個好友,是男的,就叫他乙好了。乙的老爸是大學教授,恩…教化學的,老媽是醫生,都是高學歷,在地方上也是個望族,聽說還有祖先曾中過舉人,掛著個甚麼紅榜。雖然還有個妹妹,不過家裡重男輕女的意識還是有那麼一丁點存在,所以全家人其實都對他抱持著很高的期待。」
「可惜的是,這傢伙就是個典型的二世祖,科科考科科掛,書本來就不認真念了,看到成績這樣乾脆連課都不想上。他的爸媽當然氣得要命,少不了幾頓好打,把他轉了幾間學校軟磨硬泡好歹是畢了業,還花了筆錢弄了個高中給他念。
妹妹就不一樣了,爸媽從沒要求過她甚麼,她的成績卻一直維持在全校前三名。乙本來只知道妹妹比他優秀,直到某次,意外看到了妹妹的成績單,才曉得兩個人的境界根本是天差地遠。妹妹甚麼都強,他卻甚麼都差,除了英文,因為兩個人都是從小就學,所以他的程度還能唬唬同學、應付考試。」
「上高中後,不知道領悟了甚麼,他忽然變得十分安分,不翹課也不打混。然而前幾年的光陰虛擲不是這麼快就能補回來,他的成績勉強只能搆上中等。他的爸媽卻依舊十分高興,對這不成材的兒子重新燃起希望。
三年後,要填志願了,他們期盼乙能念上國立大學的外文系,乙卻跑去報了軍校。」
其實他從來沒有想過要處處和爸媽唱反調,只是他覺得對於妹妹,在家庭的扭曲觀念下,感到歉意和難以形容的自卑。
他年紀較長卻不比妹妹懂得多,妹妹的優秀卻不能受到家人的重視。這已經成了說不出口的可悲心結,他們只能沉默的較勁。
所以他報了軍校,成績要求不高,管理嚴格又有薪餉,最重要的是,和妹妹走的必定是不同體系,再也沒有比較可言。
我忽然感到很睏,打了個哈欠,想再說些什麼,嘴唇蠕動幾下竟張不開。明明才醒著沒幾個小時而已,倦意卻十分強烈,我努力想保持清醒,但眼皮越來越重,頭一歪竟然就睡著了。
再睜眼又是隔日,我伸了個大大的懶腰,姿勢難看的從地板上爬起來。本想繼續昨天的話題,跟手道了早安後我卻忽然發現那洞好像多了幾條裂縫。
不是好像,真的多了,沿著手腕處往外輻散。我趕緊把石塊撥開,一下又推進一步,半截小臂露了出來。
越來越有過關斬將的感覺了,我振奮起來,直覺就是繼續講下去。
「說到哪了……喔,我想起來了,他上了軍校。雖然紀律真的蠻嚴格,但也少了那些亂七八糟的事,認識了一輩子都交心的好朋友,簡直如魚得水。可在大三時,他卻做了一件錯事,錯得離譜。」
「倒不是打架鬧事,沒那麼幼稚了,是喜歡上了一個人。喜歡本身當然是沒有錯的,有錯的是喜歡『誰』。
對方是老師,這已經夠絕了,最絕的還是個『男』老師。在那個時候,民風非常保守,他也知道自己與眾不同,所以都隱瞞起來了。但是隨著資訊接觸越多,他的世界也跟著開闊。二十歲,覺得自己有承擔一切的能力,既然愛上了那也是沒辦法的事。雖說如此,他也沒多做甚麼踰矩的事,只是不曉得為甚麼來往的書信會到校方手裡。」
「事情剛傳開的時候,不經意總能聽到背後的竊竊私語,那些天他甚至懷疑所有人都用異樣的眼光在看著他,但他從沒想過要退縮。
只是,連他都受不了,他那好面子的父母怎麼可能受的了?
沒過幾天,老媽從家裡打電話過來,只說了我們相信你不是、別擔心會支持你,卻不問他真假。他想說開一切,剛開口就被打斷了。
別做讓我們傷心的事。
他後知後覺的想反駁,電話卻已經掛斷了。老媽不需要答案也不想要聽到,只要結果是他們所預期,這樣就好了。他忽然有股極大的失落,再如何我行我素他也不得不承認,原來家人的認同對他是如此重要。
在他成長過程,爸媽提供了他太多資源,他不能只為了自己而毀了他們辛苦建立的名望。」
「所以他很快的妥協了,他知道他的爸媽連家族聚會都沒有臉去,因為親友不懷好意的窺探,人人正等著見縫插針。除非他某一天帶回一個符合的了家世背景的女孩,向全世界宣布過去只是年少輕狂。
有著父母撐腰,這件事的影響沒有很大,他繼續念書,老師卻被提早解聘,離開時他沒敢道別。
因為他心中有愧,當初是誰信誓旦旦的保證永遠不會放開手。」
所有人都沒有錯,有錯的是根深蒂固的觀念,有錯的是未曾考慮到這些的他。
他順利的畢業,服完志願役後申請退伍,用存下來的錢報名了補習班,想再進修外語。
我停下來,這次睡意來的更早,我配合的閉上眼睛。
「前次忘了說,中間其實還出了場車禍,對方開著小貨車闖紅燈。他被撞的左腿輕微骨折,醫生說沒事,年輕人很快就好,打了個石膏就讓他出院。」
我一邊清石塊一邊說道。
現下已經看的到整隻小臂和肘關節了,我原本假想屍體的手是折曲著擺的,但挖開來卻是伸的直直的,看來這牆厚度超過我的估計。
「回到自己家後,做甚麼事都很不方便,走路需要撐拐杖,撐久了腋下都會磨破皮,一碰就痛。剛開始還有朋友來陪他聊天,但是漸漸的,就只剩下他媽媽每天晚上醫院下班後,順道過來看看他的狀況。
明明只維持一個月就拆石膏,他卻覺得漫長的像幾個世紀。人在脆弱的時候特別多愁善感,他敏銳的察覺到,不管未來如何,爸媽都會扶持著彼此走下去,可是這依偎的背影中不會有他。親朋好友們就不用說了,他們有自己的生活,不可能隨時關心他、陪伴他。他可以選擇就這樣下去,可是他偶爾也會想著要有個家。」
我頓了頓,是了,記憶就是到這裡斷的。那時怎麼想也想不起來,但他們現在居然全回來了。
原來這才是獎勵,我挖開了我的心牆,拿回了我的噩夢。
「他竟在補習班看到了老師的名字。後來想想,其實這也不太奇怪。那是間全國有名的補習班,老師又是留學歸國的,即使無法待在學校教書,在私人公司還是不難找到工作。
對方看到他時也十分驚訝,不過馬上就轉為生疏的禮貌問候。這是應該的,發生過那麼尷尬的事。」
費了一番功夫,他把他腰折的初戀追了回來,那份狂喜不是任何言語可以形容。老媽沒有多說甚麼,到這個年紀大概也覺得兒子有個伴比甚麼都沒有要來的好。他沒去刺激老爸,如果別人無法接受,那為甚麼要強迫別人接受呢?
不論如何,他覺得這樣的生活就非常足夠,有房子有薪水,陪著他的是他執意要留的人。
我想繼續說下去,可聲音卻顫抖至極,不知何時眼淚已糊了滿臉,我的視野全是一片模糊的光。
地板在晃動,我隱約看到那隻手慢慢的抬起來,朝我伸著不動。我抹開眼淚鼻涕,走向前去。它四指合攏,微微側著,看起來就像是握手的前奏。
那天我們並肩走著,聊了甚麼我早就完全記不得了。認識得越久,對話內容自然也會越瑣碎。
不過緊緊握著的手我卻一點沒忘,那是一隻指節分明、指頭修長的手。
我向前拉住了那隻手,再也無法忍耐的嚎啕大哭。
我連你的最後一面都沒能見,因為你就在我面前被撞得面目全非;說好要牽一輩子的手,卻還是在那瞬間放開。
炫目到刺眼的光從破裂的牆灑了進來。黑板上斗大的William Shakespeare,台下的學生早就昏昏欲睡。
老師放下書,無奈地停了下來。好吧,我來演一齣羅密歐與假音茱麗葉提振大家精神。
看著老師翹著蓮花指,破音的喊著羅密歐羅密歐,你為甚麼是羅密歐,所有人一下都清醒了,底下熱鬧了起來。
醒了吧,醒了我們來上課。
底下的人開始躁動,老師擺了擺手。
“Pain is inevitable. Suffering is optional.”
這世界上愛你的人,不會只有你的情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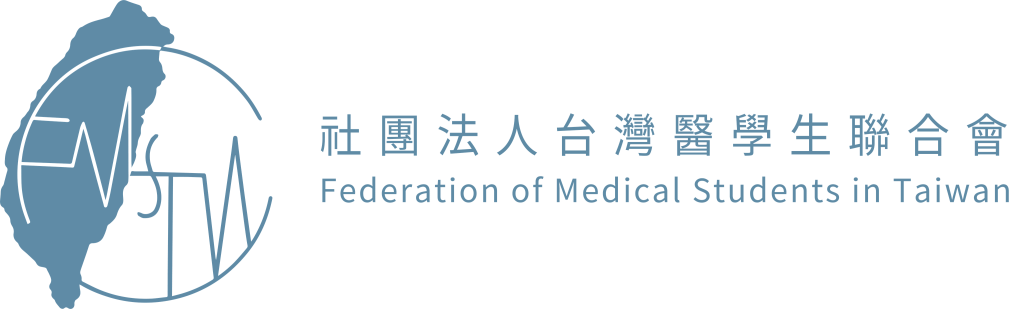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