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小說組佳作]健二《原諒》
我是李勝武,今年二十四歲,身高一百七十八公分,體重七十公斤,目前在台北 市某醫學中心擔任實習醫師。每當被人問起日常娛樂這種瑣事,假若回答「每天 慢跑五公里,一、三、五重訓」這樣的答案,免不了被投以「生活還真是苦悶啊」 這樣同情的眼光。因此我還會再補充「啊,平常也喜歡讀小說、聽 ICRT 廣播之 類的」,接著對方就會稍微抬起下巴、聲調上揚地說「喔!文青」,然後結束話題, 拿出智慧型手機百無聊賴地滑過聊天軟體和社群網站的頁面。
說起來我也只是如實回答生活的一部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對彼此的認 識越來越侷限於特定的觀點,假若像我這樣回答,過不久整個護理站和同梯的實 習醫師間就會不自主地認定「那個人是個文青噢」、「咦——不過還真的有點像」、 「那他有沒有女朋友啊?」對於這樣的談論我並不會多作回應,畢竟那邊是工作, 從這裡開始是私生活,對於這樣的劃分我相當重視,或許這種態度也有自負的成 分,不過我認為社會上對個人生活的此種認定早在超過半世紀前就被超現實主義 者布荷東在震撼之美的三種型態論述中提示過:擬態、終止和客觀機遇。所以, 我只是在名為醫院的場所扮演我想像中的一種角色,然後在範圍內狹隘地給予定 義轉述出來,別人再客觀地全部承受而已。只要我踏出醫院這個畫框似的物件, 我同大多數的同事便互不相識,就算他們也在同一家知名健身房上飛輪課程而見 到我,想必也無法立即將穿著緊身運動衫和束褲的我和身著白袍、淡藍色襯衫與 黑色西裝褲的形象連在一起……但我也不確定我是否能夠如<人子>裡老師父 強調的那般分辨是非,畢竟城市人們連自身的命題都苦思未果,遑論他人的身 象。
寫到這裡,料想大多數的人難免認定我乖僻,或許也有人願意試著理解而繼續讀 下去,所以我先做個聲明,在精神面上,我都只是個比較喜歡女體的普通男子, 然而——若沒有這個轉折該有多好,不過這樣想只是徒然——自從小學六年級被 田徑隊教練賞過巴掌後,我在生理反應上便無法再順利地做為男人。
「我們可以慢慢探討,不妨先將你現在思考的事情一件一件慢慢寫下來怎麼 樣?」、「這是一種精神官能症,我覺得你需要認知治療的幫忙」、「你一點也不喜 歡你自己」,心理治療師和精神科醫師會給這樣的答案,他們的確跳脫精神分析 的框架阻卻各種令我偏離群眾生活的因子,對此我萬般感激,不過——你會不會 想告訴我周慕雲在《花樣年華》裡傾訴秘密的樹洞所在?或許那可以從根本解決 一些問題也說不定,也或者那將是枉然——很多事情、非常多事情,就像契訶夫 之槍,一旦造成什麼空洞,便非在人生末了前周致什麼結果才好。所以我不排拒, 我只求哀悼,像芙烈達‧卡蘿那樣因愛的逝去而憂鬱,因而剃髮、穿上戀人的西 裝……你若路過喪家,且看他們莫不也反覆摺著紙蓮花沉澱心思,那都是緬懷的 形式罷。
因此我也不歸咎什麼,畢竟這個社會連第六根手指這種優勢遺傳也多半採取手術 切除的做法,那切下來的手指到哪去了?電視節目只當作怪談一樣地帶過,「人 類學家考據認為五根手指的抓握最能符合器具使用的需求,換句話說,不需要第 六根手指什麼的」;文學作品大概也朦朧不明地消費過所謂遺傳學的發現和新進 展,並賦予時代留下的蹤跡。可是那之後的我們究竟能走到哪裡?跨出臺灣這個 島嶼或許可以找到消失的第六根手指,很多人這樣想著走著,絕大多數還是斷不 了根深蒂固的宿命,被神祇也好、親信也好,像夢迴一般地回歸塵土,飛啊晃地 搖曳著、乘著風——我想說的是,就連我於自身的遭遇都沒有批判的空間,否則 我不配為人,是以我只書寫,決不倒置南北、就東論西。
「你覺得你這樣會不會令自己置身危險之中?」這是怎樣的問題啊!假若我身陷 囹圄、倘若同四零年代風行那般接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肯定的前額葉手術,我可 能再也無法讓這般敘述於我心底活過來……那是一種執念!否則莫非我執從不 存在?不、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戰後民主主義是由白大象從印度王室載運到東亞, 然後再一聲悶吭也沒有地帶走似的,那的確存在過。歷史敘述本身儘管難以否定 而只能被笨拙地詮釋,但我們卻不能貪求安適而逃避見證歷史。克勞德‧蘭茲曼 的《咻——啊》以長達九小時的記錄片闡明語言見證的難度並讓我們從納粹集中 營外部見證到內部,從而驚愕地覺察,內部證人竟不存在。從集中營生還的人們 終究不同於『內部的亡者』,因此大屠殺是沒有證人的絕對歷史事件。你讀伊格 言走到威瑪後寫的文章,「生」的氣味竟然無聲無息化為明、暗皆意義不明的量 體,你會覺得生比死來得沉重太多。
「不會,我有一些方法……他們會以為我在做田野調查,他們會很樂意讓我訪問。 不過就如同你猜想的,我對那些問題的答案不感興趣,我抄寫那些資訊也不會做 實際運用和分析,但那些問題的問法會依經驗累積而變得熟練這無庸置疑……」 我停頓了一下,畢竟這不是容易說出口的事,但我在那個時間點不得不說,必須 有人將那沉重承受下去才行,一開始以為那是簡單的事……就算李勝武這個二十 四歲的青年在醫學系的成績只能算是中上、臨床表現也絕對算不上積極靈敏,不 過以十二歲那年做為分水嶺以來卻也無機質地處理大量青春期性慾引起的干擾 而在某些老師心裡留下上進的印象,然後以學校推薦面試入學的方式考進國立的 醫學院,不管如何都不被認為是腦袋有問題的人,或許某些部份多少有過份偏執 的傾向,不過那都是有待集體社會規訓的個人化的稜角,比起什麼都不懂而過份 發表意見卻毫無行動力的少年,這種看似深沉的性格反而被視為內省的具現。「不 過你還是得像那個誰……還是要內斂一點才好,盡量跟別人一樣。」曾因某事而 被如此訓誡,然而那只是一個行為實驗,看起來是莽撞而一廂情願的行為,從長 輩的角度來看絕對是挑釁式、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卻拗成當為與不當為的假議題。 就像女高中生選擇塗上粉黃色與黑色相間的指甲油一般,只是選擇適合自身的顏
色精準地塗上手指而已,真正的問題不在指甲油、更不是塗了指甲油的手指,或 許從那個順序看事情會比較容易,不過正如世間的經驗顯示,深掘第一眼看到的 東西絕對不會有好結果。後來有些人想到用去光水,塗抹潔淨,從此看不見。不 會有老師在放學後尾隨那個女學生吧?想到眼前的陌生女人過去也當過女學生, 撐著過於貼身的白色制服、袒出廉價內衣的鋼圈,會不會請與自身年紀相近的女 性教師同事代為糾勸那位女學生呢?不管如何,後來女學生終究換了指甲油的顏 色,同街角電線桿上的選舉文宣融為一體。
「那些是怎樣的問題?問過那些問題之後呢?你會做什麼?」問題的答案與答案 的問題都會膨脹。當時我腦中浮現國中時期被班上同學欺凌的女同學,我們都喚 她水星人。水星人從來就沒有做錯過什麼事,只是——這種轉折容易讓人逃避真 相,在這個時間點面對霸凌議題還是照著回憶走罷,雖然這一點也不科學,然而 面對文字我們只能忠實……約莫在中學二年級的夏天,國中班導師曾經令全班閉 上眼,要言行嘲諷水星人的同學們都站起來,不消說這作為本身是一種值得議論 的「文本」,如果你像我一般身為欺負者卻沒有站起來承認,你會覺得周圍同學 的衣服磨擦聲窸窸窣窣就像「眾聲效應」這種小說手法般此起彼落,那聲音化作 光影、穿過眼皮投射到視網膜、藉由視神經傳遞電訊號到枕葉使大腦成像,然而 那是一個徹底的謊言。我相信在場甚至也有同學好奇睜眼瞅瞅到底有誰,但事隔 十年我只覺得站起來的人、坐著的人(包含我)儼然是後現代符碼的展演。後來 班導師笞責站起來的人,要他們和水星人道歉,然而水星人被嘲笑的捲髮和豐滿 的身體仍舊存續在那扭曲的時間裡。我不會忘記水星人那雙怨懟的大眼印記受罰 者蜷縮如現代舞葛蘭姆技巧般身型的模樣。
我多麼希望水星人轉身叫喚我的名字,當眾怒罵:「平常在書店遇到你,你總是 跟我聊天,但我都知道你只是假惺惺。你只是因為罪惡感、因為我爸媽和你家人 熟識。我其實都知道,那些嘲諷我的歌詞歌曲、甚至是舞蹈,都是你帶頭起鬨的!」
我想道歉。
然而班導師那樣的處理方式讓我與我的行為本身仿如從未存在過。我之所以欺負 水星人是因為我不想被欺負。我知道我很奇怪,讀書的時候總是要把課本由下到 上整齊劃一和桌腳對齊排列;將保特瓶瓶蓋旋緊十秒確定不會滴漏才將瓶身擺放 到十點鐘方向;鉛筆盒要安放在正前方,距離桌緣大約七公分;課本攤開後要用 藍色水性原子筆在課本封面點一個小點,告訴自己調整到讀書的狀態;為了確認 自己這一科要讀多久,所以將身體傾斜二十五度,確認時鐘的秒針和分針重疊在 一起,然後注視時針的假想延長線所指向的第一個物體,凝視五秒鐘。
我很害怕被同學發現我有這樣的習慣。某些人隨處隨地拿起課本啪一聲就可以有
效率地吸收所謂義務教育要求的知能和對應的考試技巧,但我必得疑神疑鬼地透 過這樣的起始儀式才能真正開始閱讀課本的文字。越是擔憂被後不知哪來的眼光, 我就愈發緊繃地讓儀式更繁複以追求當時自認的身心靈平衡。
……只有在打籃球和自瀆的時候我才不必如此計算每分每秒。我知道我在追求男 性筋肉的美,那種被初春荷爾蒙過度渲染的童稚美,我知道當時身邊的男同學和 我身上都有那樣稍縱即逝而不真實的東西。為了讓那種邁向男人的不成熟況味實 體化,我站到男同學那邊成為欺負者。
我是懷抱多大的罪惡感和苦衷,那樣的心思卻被班導師用問卷調查式的處罰消卻 無蹤。那種方式將學生二分為「沒問題的好學生」和「受處罰的壞學生」,卻沒 有留太多餘地給水星人再去責怪他人。那像是詛咒一般。水星人畢業後十年的團 體生活據說沒比中學時更好。我曾經在家鄉的麵攤和她偶遇,兩頰內凹、雙眼銳 利,中學時代受欺凌的創傷絕對在原本豐滿的身體上狠狠踐踏過吧。
我想贖罪。
「我會問他們有沒有三高和相關的家族遺傳、有沒有抽菸喝酒吃檳榔、有沒有香 港腳……,有時候會問有沒有 B 肝 C 肝——就是一些公衛問卷會去問的東西,套 用一些醫學名詞,我有參加偏遠地區的服務隊,我知道那個模式,將質性或量性 資料整理、統計後就會有數據可以進一步分析。」
「你真的有去統計那些數據嗎?」
「有,非常粗略地。輸入電腦簡單跑一下迴歸,看相關係數,稍微掌握那個結果 顯現出來的樣貌,然後對照每位個案,就會讓前置問答的過程更流暢、更有說服 力,現代人都關心健康議題,只要取得個案的信任,後面要做什麼就會比較好說 話了。」
「要不要試著講出來:接下來你會做什麼?」
「我……我、我會請他們脫鞋,讓我看一下他們鞋子的材質還有款式,如果狀況 許可的話,可能還會請他們讓我用手機拍照,拍鞋子,當做記錄。附帶一提,我 一開始就會和他們說清楚,這訪談是匿名的,資料也不會挪作他用,也不會丟出 太個人性的問題,比方生日、地址、身分證字號,很多人對這些資料非常敏感, 甚至會率先表示不方便提供這些資訊,所以從我這裡先做這樣的聲明實際上會比 較容易取得交互立場上的發球權。」
那些畫質粗糙的皮鞋照片於我而言究竟有什麼意義?套用精神分析的脈絡又能 有怎樣的結論?或許可以將那些照片列印在硬紙板上,按照日期排列,由左到右, 十張一列;由上到下,十張一排——就如同十進位或者直線時間軸等概念,儘管 那只是方便我們生活而認定的規則,百千年看來卻也無罣礙地令我們生活過來。 這些皮鞋的主人們究竟是怎樣的臉孔、談吐、性格,打從照片被拍攝的那一刻開 始就不被記得,重要的是那些皮鞋被那些可能是警察、可能是保全、可能是房仲 業務的男子們「穿過」,他們的個人特質被排拒在硬紙板上的照片之外,真正重 要的符碼只來自警察、保全和房仲業務男子們通過襯衫和西裝褲的布料(尤其是 人造纖維和尼龍混紡)網格裡散發的男性費洛蒙和蘊含肢體蠻力與精神毅力的軀 體。試想我們通過蒙德里安的格子窺視從來就不存在我們意識裡的人。我們從外 面開始凝視,然後與他們羅織一個泛義而真實性未定的健康座標;他們脫下穿著 工作一整天的皮鞋,皮鞋裡散發出時間通過人體而遺落在鞋坑這個限制場域的酸 臭與溫熱,手機相機的長方形框架發散一股驅動令他們不願入鏡而徒留一隻由製 鞋工廠大量生產卻印記了擁有者生活點滴的「舊皮鞋」在視野內,然而那只被框 架截取了的皮鞋卻和梵谷畫的破舊鞋子不一樣!
梵谷畫作裡鞋子的補釘展現工作勞動的特質進而誘使我們去想像鞋子的主人及 其存於畫框之外那些饒富詩意而意在言外的故事;不過「舊皮鞋」的擁有者們卻 拒絕在照片甚至是印刷出來的圖片裡表現其獨特性,因而使這些皮鞋照片乍看並 不具原創性。我們透過大量的人為排列,令這些款式各不相同、新舊程度不一、 擁有者職業各異的男士皮鞋照片表現出驚人的統一特質:這些皮鞋是去身分化的 黑色物體。硬紙板的邊線不是印象派的畫框,而是風格派的方格,這些方格本身 即傳達強烈的純粹性,因而使方格內外的物體被投以全然的無關心性與無目的性。 那些皮鞋的擁有者是原始、陽剛符號積累而成的後現代理念。他們透過問答,從 衣物的網格裡讓私密的個人資訊出走、毀滅,接著依從我的請求脫下皮鞋,轉化 為普世價值重複塑型的眾生相。那些擁有者正在進行一種近似於「扮裝」的過程, 他們化身為十二年前給李勝武掌摑的田徑隊教練,同時也是手持藤條處罰壞學生 的班級導師。然而這與杜象的扮裝影像差異在於,我只不帶批判性地記錄為了扮 裝而「脫掉」的舊皮鞋,並且只能重複透過問答與拍攝敦促自己正視過去經歷的 無言。
「請他們脫掉皮鞋之後還會做什麼?」
「我會在我帶的筆記本上劃出一個三乘三的表格,上方第一列的第二和第三格分 別註記右腳和左腳;左側第一行的第二和第三格接連填上濕度和氣味。我將我的 手掌貼在對方的腳底,感受襪布織理表面的汗膩程度;再移動鼻尖到距離對方腳 趾約十五公分的地方,吸納摻雜皮革和腳氣的濃重味道。我會量化這些指標,一 分最低,五分最高,依照左腳、右腳的分項填入表格。有些人兩腳的味道和濕度
會有顯著的差異,也有些人幾乎是一樣的。他們會疑惑,只是個學生研究為何會 做到如此細微而超乎常人想像的程度?甚至也有極少數人曾經針對一分到五分 的量化方式提出質疑,認為那樣的量化方式只是個人感覺,不能當作客觀的量 尺——他們可能時不時提出各種問題,但也有不少人表示讚許。將近一半的受訪 者對於這樣詳細的記錄和觸碰感到受寵若驚,甚至開始分享他們在自身工作中經 受的壓力,以及無可避免的睡眠缺乏、運動不足。我不針對他們的抒情加以評斷 或回應,我用專注的眼神榨取我自身對受訪者所能及的最後一點人文關懷,他們 有的會因此露出放鬆的微笑。『你也真是辛苦了』隨著我的訪談技巧越精進,這 樣的回饋越來越多。」
「嗯……那你會不會跟蹤他們?你會不會有拿取他們鞋子或襪子的動作?無論
如何,不要讓自己置身在觸法的風險之中。」
「我不會跟蹤他們。法律方面……我不知道,現在對於個人隱私的規範越來越嚴 格,說起來這樣詳細的訪談應該需要簽署同意書對嗎?唉……就連外在力量都敦 促我要讓這出外訪談的蒐集過程繁複化。我不會有偷取的動作!我知道那後果不 堪設想。我希望你能理解,我這會兒來這裡講這些無非是希望得到一些幫助。也 不是每一個外出訪談的晚上我都能如此順利,拒訪率大約有四成——我從那樣的 過程感受到的是人情的溫暖和殘忍。試想門外那些來同你要替你憂的病人,他們 的意圖是從你這裡『獲取』那種藥,是自個兒騎車開車或搭公車來的,或許一路 上早就慌張地瀕臨過度換氣症候群那樣的情狀,但他們還是來看你了對嗎?就帶 著淡藍色的健保卡,像以往的蒸氣火車乘客那樣頂著溽暑般的思緒等螢幕上的號 碼對應到自己,暫且賦予自身一具足以支撐越過一節車廂裡擁擠人潮的軀體。你 不知道自己是列車長還是乘客,因為他們往往要你削足適履。無論如何,你最終 會在給與不給替你憂之間做一番思忖,但那不表示給予便是溫暖、不給就是殘忍 的作為。給與不給的問題在於你是不是看透前置在他們身前的杜象大玻璃,你要 運用語氣和眼神流露你對病人的『反窺視』,你實際上變成他們羅列的索引之一, 你必須讓他們知道這一點,但你卻也得讓你們正在共譜的故事進行下去,所以你 必須真正看見而後假裝看見,不是佯裝沒看見!他們能夠發現你那番心思,要知 道那點意欲的流動足以超越溫暖和殘忍而真正救贖他們,令他們感到被理解與被 接納。那些言詞和行為都可以被輕易拆解,這點你我都是很清楚的,不過學理上 最近也傾向不那麼做了的樣子,因為那會讓事物本來的全體像變質,就如同石膏 像翻做成青銅,直覺上究竟比較容易接受石膏像為原作的邏輯,但經由藝匠準確 翻製的過程是否能將藝術家的原創性精神傳達出來?假若可行,那就得再進一步 探討複製品。這樣說或許不甚恰當,不過某種程度上我們也是醫匠,依循共同的 準則在有限的範圍內探尋突破的可能性。我們講求技術的精熟,同時成立繁複的 系統讓這些技術成為封閉而不只是說明書那種案牘文書可以記載詳盡的學理。我 們停下來討論一個議題,你認為手術可以和雕塑類比嗎?二十世紀初青銅作品翻
製專家李梅特的文書寫著:『我等著檢驗奧斯汀送交給我的羅丹夫人頭像的青銅 翻製品,翻製得還不壞,但照我看來,雕琢的工作有很多缺點。我們難以評判這 件相當單純的作品……』李梅特的文書暗示身為藝術家的羅丹本人並非如我們設 想般嚴格地監控那些翻製物的品質。不過再怎樣雄辯的暗喻也抵不過病人乃為人 這再明晰也不過的真實……儘管你我都能從工作中體會到病人的身分是流轉的、 他們的照護模式也是變動的、甚至連我們的思慮也都是不定性的,然而我們只能 如<花與愛麗絲>電影裡雨中輪舞那般不間斷地自我辯證。」
「所以對於拍攝皮鞋的照片、嗅聞穿過一整天的襪子這兩件事對你而言是否真為 你夜晚四處驅車尋訪的目的?」
「是,卻也不是……我到底在追求什麼?我也是在幾個月前某一回的外出訪談 才開始理解。對方是一個房屋仲介,三十出頭。我到他店裡拜訪的時候將近晚上 十一點,他還沒下班,從他滿是皺摺的白襯衫、半鬆開的黃色領帶和佈滿血絲的 眼白,我可以確定他絕對奔波了一整天,無論體力或精神上,應該都處於慢性疲 勞的狀態。儘管如此,他仍舊撥出幾分鐘讓我進行訪談,對於一切的個人健康問 題,他都能在問題丟出來後不假思索地回答。想必他就算多麼勞累,只要面對客 人都能讓大腦高速運轉以令對答內容不失準頭。懷抱那樣敬佩的心情,我謹慎對 他提出脫鞋的請求,儘管嘴上嘟嚷那有些奇怪,他還是把鞋脫了,讓我拍照存底。 不過,就在我畫出九宮格,與他提出觸碰腳底、嗅聞襪子的要求時,他一反親切 態度,激烈地起身跺腳說,『很抱歉,我沒有這樣的興趣,這很奇怪!』我當下 愣忡了——這男人知道我究竟在做什麼!他理解我!我甚至大膽假設,他先前也 曾被人如是要求,否則他怎能在我們這短暫的訪談中令主體客體易位?他原先是 受訪的客體,他只是不具名的舊鞋主人從屬物,然而卻在轉瞬間反證我只不過是 眾多複製品之一!那基於我對自己獨特性的自信所羅列的原創性問卷和經由時 間積累的親身訪談技巧倏地在那言詞迸發的鏗鏘之間灰飛湮滅。我最初希冀從他 的皮鞋和襪子的形體與氣味中再現我經受田徑隊教練巴掌後所獲致的感官經驗, 當下竟顯得無足輕重。我追尋的究竟是體罰創傷的心理重建抑或是自憐自艾的慢 性自我戕害?而我到底是冒充醫者的角色行自我療癒的消費之實,還是陷入病態 的思緒泥淖中戀棧病人的身分而難以自拔?我原先在自身建立的『秩序』如今已 不可靠,我也不再能穩當地羅列任何儀式性的思考或行動以制限我瀕臨失控的精 神。」
「田徑隊教練對你甩巴掌之後發生了什麼事?……能不能詳細描述你提到的感
官經驗?」
說明過剩的剖析將成為乾巴巴而無版權的寓言,那樣的文字組成只背負深沉的悲 哀,卻罔顧色彩、織理和平面化帶來的痛楚。那是不行的。人們會以為主角豐足
得很為何無病呻吟!是否看不慣金閣寺那般巔巍的美而轉向欣賞平安神宮在冬 後春暖盛開的乍現櫻花?如此愛好在腦海裡翻騰這般辯證,難怪鬧出病來。還是 快快與大夥兒出遠遊,前往泰國那蒸煙瀰漫的大王椰子間迷亂地啜飲淡橘色的檸 檬汁。嘿,看好哪,台灣的檸檬汁是混濁的白色,不代表全世界亦同如是。我們 有定靜思安的彌勒佛,但你去臥佛寺,乘著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地盪過去,你會 看見好多臥佛圖像,拿不準是要覽遍這幾許幅的擬真攝像同臥佛真身告密,或者 同臥佛對影成三人……不過臥佛啊臥佛,為何我無法將祢盡收眼底呢?祢究竟以 怎樣的姿態存續於我所不知的空間?那個空間若是由外而內搗入芯一般的東西, 會不會滲出血來?若真有鮮紅色的血,你會不會憐憫那其中也有生命流瀉千里? 還是你會要我到印度河畔,用自身的口鼻去包被那深水。我明白河包容了我們, 我還曉得河底有多冷。因此我再也禁不起否定,但也不想經受讚許,這是多麼矛 盾的心緒!那年黏貼在田徑隊教練筋肉上排汗纖維的氣味令我中毒,令我不配為 人。我多麼反證這點。我一直付諸行動探尋任何推翻的可能,卻不知不覺過度磨 耗自己。
讀書、跑步、英文。讀書跑步、英文。讀書、跑步英文。
讀書跑步英文。跑步、讀書英文。英文、讀書跑步。跑步英文讀書。
跑、英、讀。讀、跑、英。英、讀、跑。
英讀跑。讀跑英。跑英讀。
英讀跑讀跑讀英。
我實踐毫無喘息的刻苦生活以雕塑我的腦迴,我不得不。我的腳被教練壓著每天 做一千個仰臥起坐,我的手撐住身體每天做五百個伏地挺身。我的身體不是我的。 我只能倚賴我心中的神,神的所在或許同印度河底一般清冷,不過神總是在那裏 守望著。
我家那座神龕供著文身赤面的關公,關公神像後的彩繪圖畫乃玉皇大帝及其麾下 諸位天神地祇。田徑隊訓練結束回到家中沖過澡後,我總穿著貼身的白色背心和 紺色運動褲,雙膝跪在距神龕前約一公尺的磁磚上大磕三個響頭,隨後在口中囈 語:「神哪,還有我心中的我哪,我是李勝武,你們聽得見我、看得見我嗎?今 天我表現得怎麼樣呢?無論如何我都盡力了,希望你們能肯定我。若我有做錯什 麼、有哪裡不周到,容我跪趴在你們尊前懺悔。期盼明日能有全新的開始、能有 好事發生。求求你們了。」
然而那幾年的夜裡我終究睡不沉。關上房門、插上小夜燈的六坪房間只有書桌和 衣櫃影子在棉被上的延長,那令我想起過往田徑隊窄小的器材間鐵窗射入的落日 餘暉。夕陽西斜時原是教職人員和學生的返家時刻,然而田徑隊員還得在跑道上 挑戰光影與三度空間互動的極限。若非教練對短跑速度和身體能力嚴格要求,我
其實更憧憬能自如收放呼吸深淺的長距離跑者。教練總一再提醒起跑時要放低身 體重心,才能在鳴槍後如疾風迅雷般奔馳,不過我再怎麼蹲低都刮不起教練急欲 看見的那陣暴風。
『蹲低蹲低!大腿夾緊、屁股翹高!』
汗水灑落在跑道上蒸散出一股乾辣辛臭的氣味,橘紅色的火球在地平線那端只賸 半邊,銀灰色的檸檬月懸掛在天際另一邊、像一顆偌大的飯粒。教練的喝令在我 耳邊碰碰碰地鼓動,我卻瞧著藍紫色晚霞裡一線細長的飛機雲,瞧得出了神。沒 幾秒後我只覺一面黑暗襲來,一股熱狠的勁道幾乎就要扯裂我的右臉頰,我耳根 嗡嗡地響一陣後隨即失去平衡,滑稽地仰倒朝天。
『中看不中用!』
我連滾帶爬地追著教練到器材間。當時我完全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只見教練拿 出裝著平價西裝的紙袋,一言不發地脫下汗濕的貼身灰色運動背心,蹬掉腳上的 藍色愛迪達跑鞋,刷地一聲褪下左腳的黑色棉質毛巾底運動襪,俐落地從紙袋裡 抓出一只深藍色的聚酯纖維紳士襪,教練露出百無聊賴的神情套上那織物後,以 揀拾運動襪的那隻手臂搭肩對我說:『教練是希望你好。』
教練說那番話的同時我聞到來自教練手臂間的一股橡膠球鞋味和腳汗味作勢要 環繞我的軀體,我因排拒那股異味對鼻腔的侵襲而低下頭,只見教練裹著深色襪 布的腳趾張牙舞爪似地好似在指責我是多麼令人失望。我全身癱軟地坐在器材間 的長椅上,看著教練背向我換上一身同田徑場是一點干係也沒有的西裝,然後喀 啦喀啦地踩著黑色方頭皮鞋走出器材間離我而去。我驀然感到一陣鼻酸,燒燙的 淚液奪眶而出——
「你必須立刻接受治療。」
「那麼……關於臨床工作的部分……我是想說,以我這樣的情形,是不是無法勝 任臨床工作……?」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面對這個問題。我就直白說了,你並不喜歡你自己。」 「……天哪!怎麼會……為什麼你可以在短短的談話中立刻掌握這個實情呢?」 「這也是我們訓練的一部分。」
「我的確不喜歡我自己。我不喜歡我的身體、我覺得我由內而外全都爛成一 團……我也不想一直到處騙人,可是我無法控制——每次訪談後我總是陷入巨大 的空虛和罪惡感……到底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如果可以歸咎於誰就好,但我不知 道我可以怪誰……」
「無論你是怎樣的人,你都必須學著將那個當作事實坦然接受,你才能承受。」 「先接受、然後才能承受嗎?」
「你要先接受你自己,臨床工作什麼的、你才有辦法承受。你必須立刻接受治療, 先把你自己照顧好。等會兒出去就先把藥吃了。」
我想起畢卡索的畫作<格爾尼卡>中倒下的戰士,他們宛若被拔黜的聖體,究竟 是被速寫而周致一幅時代經驗的概括插畫、還是被描繪以宣稱藝術家對自身時空 的深思?非關抽象與無實證關係的差異,那些戰士關涉超乎輪廓之外的元素並使 之轉化。無論如何,就算是相當不同範圍的混沌,仍能構成一種秩序並保留自由 的情態吧。「我從未向你借過你控訴我破壞了的壺子,就算我借了,在你借我的 時候它已經有一個洞口。」佛洛伊德的借壺論證如是說,那麼傅科在那之後又說 了什麼呢……
停!到此為止了。我必須跳過、跳過、跳過……
我提著藥袋一跛一拐地走出醫院,看向歪斜的柏油斜坡與色調陰冷的高樓,一張 張朦朧的臉龐於我身後潮來又潮往。復康巴士從我眼角遠駛而去,若是接著那端 點向前走——
我的故事將充滿不安與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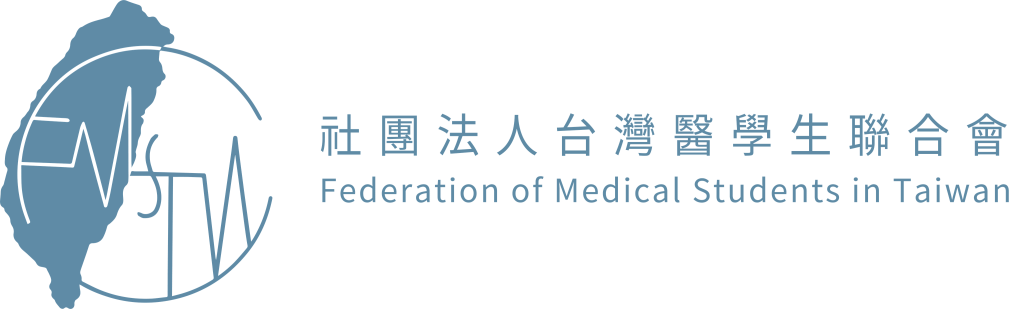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