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小說組首獎]陽明醫學四-王昱婷《早餐街》
-1-
學校外面的小路上,開了各式各樣的早餐店。
各式各樣是小屋說的,阿凱並不這麼覺得。早上六點一直到正午十二點,如果你願意來城北走走,整條農安街會發出蛋及肉片在油上炙烤的味道。有鐵鏟──每一家店都有──這邊切割、那邊撥弄的舞動。每個禮拜六,阿凱固定會從城南搭早上七點半的捷運來這,我們在車站碰頭,牽起彼此的手,然後像跟隨一場綿延無邊的喪葬車隊,安靜穿過農安街近十家的早餐店。阿凱說,在城市裡尋覓食物是很暴力的。他從小作一個茹素的人,路過每家店,看見料理台上布置的食用油和各種動物器官,都活在必須和整座大型墳場共存的恐懼中。我不像他那麼挑嘴,菜也好肉也好,只要不是醃漬到像菊石那樣千年不死的食物我都吃。但就像農安街無法決定自己的發展,我也沒辦法阻止我的胃生長到叛逆期。
生長到叛逆期的胃?聽起來怪誕,但是千真萬確的。我有一個會離家出走的胃。更準確地說,是胃把自己和食道及十二指腸以某種方式分離,穿過了骨骼肌肉層來到皮膚之外,自詡為獨立個體那般地出走。第一次我看見它這麼做,我正處在一隻手拿著電話,另一隻手要掏衛生紙的尷尬姿勢。先是感覺到有濕濕滑滑的物體,好像是一團球的形狀砸到我的腳,往下一瞥,竟然就看到史多邁──請容許我因它發展出自主性而取了名字──在房間的地板上移行,不,也許說蠕動更適合,就像平常的消化道傳送食物那樣一伸一縮的扭著,竭盡心力的往牆角爬去。我不知道史多邁是否能看到我的臉部表情轉而像暴風雪那樣慘白混亂,既擔心它會爬到窗戶邊跳下去,又害怕它偷拿我放在右手抽屜的剪刀把自己戳出好幾個洞。情急之下只好先把所有的危險物品都鎖上收好,再靜觀它的行動。幸好事後回想,史多邁可能只是不喜歡晚上的義大利麵放滿冷凍蔬菜,也不喜歡我剛吃飽就和阿凱在電話上吵架。所以當我對著手機哀求:你可不可以不要在記者的面前拿麥克風批鬥他們?都被鏡頭拍下來了。史多邁同時在我的身體裡翻攪幾下,墜落,試圖用大胃彎挺直身軀,像即將嘔吐的可憐蟲極其緩慢的往電鍋搖晃過去。
這並不是甚麼大不了的事,我試著告訴自己。史多邁喜歡插著電、但沒有按下開關的電鍋。冬天的時候我的身體常常無法維持一定的溫暖,它就愛躺進去,享受它底部剛剛好不會燙人的溫度。我通常不去驚擾它。過了一夜睡飽了,史多邁一定會回來,有時還會貼心地幫我把電鍋插頭拔掉。這個祕密我告訴過阿凱,又跟小屋說過。那時阿凱忙著寫聲明稿,質疑我為什麼還活在戒嚴時期的遺毒裡,只有小屋願意鼓勵我,這是好事啊,起碼史多邁還是我可以掌握的東西不是嗎?所以我選擇相信他。我想他說的不能掌控,就好像十歲的時候我以為自己會成為畫家,二十歲的時候卻被長輩和意識形態行銷到醫學系那樣。又比方農安街以前大概只是田埂,現在卻在二段蓋了大學和醫院。這裡上下班時間常堵車,半夜還有人為了買宵夜在這裡跟要去山上夜衝的車子發生擦撞,被對方拿棒球棍跟水果刀傷害……。不能把握的事情太多了,史多邁算起來還是跟我站在同一個陣線上的。
-2-
順著農安街一直走可以通到一棟巨型的白色建築。我帶了一盒水彩擠進電梯,小屋住在18樓。扣掉濃濃的藥水味和昏黃的陳設,他這幾天是過得像暴發戶那樣的生活。有人專程送飯,靠窗還能望見首都的五星級夜景。
「好手好腳的話……哪座大屯山群都可以看到更美的。」他躺在病床上,虛弱地說,「都怪我媽小時候要我學空手道我不肯,我現在連筆都拿不起來。你幫我帶水彩嗎?不用露出尷尬的表情,妳能來我就很高興了,妳也沒想到我會這麼嚴重吧!」
「醫生怎麼說?」
「他說手碎掉了,還警告了我很多很嚴重的後果,但我都沒聽進去。不會死倒是真的。外面這邊好痛啊,這是甚麼?」
「尺骨?」
「對,整個穿出來了。醫師說等消腫一點要幫我開刀。怎麼辦呢?期末要交五幅畫,到現在一幅都趕不出來。一直在虛度光陰。躺著,作作惡夢,然後被自己的手痛醒。」小屋用兩隻很黑很憂鬱的眼睛看著我,我以前總是在裡面看到好多色彩。「把它放這就好,明天我同學會來,也許他們能幫我想到別的方式畫畫。也許用嘴巴?妳想有可能嗎?哈哈,還是醒著好,生活雖然亂七八糟畢竟是自己的。不像夢裡會突然被丟到一個完全摸不著頭緒的地方。」他擠出了一個微笑,看我幫他把水杯注滿。
「哪,喝水。我倒覺得醒著也是摸不著頭緒的,不知不覺就被學校塞滿考試和課程。作夢的話,就連穿梭時空都不成問題。」他啜了一口杯子,「像是?」
「像是有時候會夢到小時候跟奶奶住的老眷村啊,有時候遠一點就去花蓮看太平洋。每天都不太一樣。」我尷尬地笑了笑,含糊帶過。
「阿凱知道你來看我嗎?」小屋脖子不方便轉動,但眼睛已經轉向窗外。首都多愁善感的氣候啊!城市輕輕下著雨。
「嗯。晚上吃飯的時候跟他通過電話。」
「他還好嗎?」
「老樣子。再過幾天廣場那附近有個社區要被拆掉了,這幾天他跟他的弟兄都在努力動員人馬。」看他沒有再說甚麼,我起身要打道回府。
「改天再來!希望能看見你好轉!」小屋說了聲好,濃濃的、墨魚麵條似的眉毛在跳舞。病房之外,傳來淒厲的哭聲。我不敢抬頭。前幾天上骨科的時候老師才在螢幕上播放一隻被輪胎輾過的腿,如菜市場被刀子拍扁剁爛的絞肉,他會不會也是這樣呢?這麼想著的時候,一路上又遇到好幾個穿著白袍的醫師拎著晚餐走來走去。醫院更外頭,車聲轟隆,飆車族依舊,即使入夜了也完全沒有疲憊的感覺。我一個人慢慢踱步經過農安街,招牌都暗了,也少了白天會懸浮著的熱氣和油煙,稍微抬起頭就可以看到海拔一百二十公尺的女生宿舍。
小屋說的沒錯,夜景不是甚麼稀奇的事。假如我有勇氣把窗簾捲起來,三分之一的窗景是首都點著火炬閃閃發光的樣子。但只有週末,宣跟寧跟蓉都回家,我才會把窗戶拉到最高爬到床上一邊寫著日記,一邊看著最後幾班捷運從文明上空漂過去。我也曾經看過煙火、流星還有飛機在夜空中拖著尾巴語焉不詳的消失。假如我有一雙貓的瞳孔,很遠的某個地方當有人往山的這個方向看,滿城的火樹銀花之中,他會不會獨獨被生者的凝視所吸引呢?我有時候兀自撐起下巴這樣想。是綠色的?還是棕色的?眼睛的光跟那些黃黃紅紅的霓虹燈一定都不一樣吧。
高架床下和書桌周圍的牆上掛著小屋的作品。我們熟識的這年他送過我幾張風景圖。睡前假如我很想去他筆下的山脈河川,我會牢牢地注視著那幅畫,有時真的就夢見了。夢見我站在那片風景中,小屋在天空的盡頭繼續拿著筆把草地鋪下去。認識小屋的那一天他就是這個樣子,穿著襯衫,伏在農安街轉角的飯捲專賣店桌上畫水彩。想不注意都難。在我們這群醫學院學生為主的環境,吃飯不外乎是帶共筆猛讀,從來不見來餐廳畫畫的。而且他拿的並不是速寫畫家的小型水彩盒,而是打開來比兩張A4紙還大的調色盤和分成三格的筆洗,占了整張大桌。他的手總是好幾種顏色,在紙上塗塗抹抹一會兒眉毛一皺,就順手抓了飯捲囫圇咬了幾口吞下肚。大概自己的顏料也吃了一點。
我其實也愛畫圖,雖然已經封筆多年,每次在路上看到有人在做這樣的事都還是會停下腳步觀賞。吃飯捲的時候我故意坐小屋旁邊,偷瞄他的創作過程。我以為敢在外面畫水彩的人都肯定心無旁鶩,想不到他才剛渲染完天空,竟停下筆抬頭看我,像發現獅子的羊那麼機警。我因為沒有防備,兩隻眼睛就正面對上。
「妳也畫圖嗎?」他微笑著問我。
「我嗎?不,我現在不太畫,小時候倒是很喜歡。」
「真可惜呢。」他露出很失望的表情,「不過……妳覺得這裡的山,要用褐色還是深藍色好呢?」
「嗯,如果真要問我的話,我覺得深藍色比較有空間延伸的感覺。」
「很好啊,跟我想的一樣!如果妳願意等到我畫完的話,這張就送給妳。」他看我好像備受驚嚇的樣子,又補了一句,「我說了算。反正不是甚麼值錢的東西,我也每天都畫。不差這一張。」
後來,我從飯捲店老闆娘那裏得知,小屋是附近藝術大學美術系的學生,跟我一樣大四。確定是大學生,心情就坦然許多,平常這樣無情的天氣史多邁有時候沒有吃到湯麵就會跑出來躲進電鍋。認識小屋的那天,它竟然一整個晚上都沒有鬧事。
-3-
好了。現在你開始疑惑,我是不是周旋在兩個男人之間。事實如你所想的那樣,我本人卻也不清楚原因。阿凱是我的高中同學。我們一起長大,一起補習,可以說是熬過一切地來到同個城市念大學。只不過嘛,他住的城南是政治作戰中心,被所謂不公不義的手腕操控;我住的城北則是夜景優美的邊陲小山,佈滿灌木、鳥雀和健走的老人。景物的不同使我們對生活有了最基礎上的歧異。我想那是後天註定的,像南橘北枳的故事,任何改良移植都起不了作用。
儘管這樣,他還是每周來找我,牽著我的手穿過早餐街(現在我們都這樣叫它),盡可能打破地理和時空疆界地重溫高中時光。我其實喜歡聽他偶爾談談城南那些迫遷戶的辛酸史,喝他為我帶來居民手製的,又香又醇的豆漿。歧異並不妨礙愛情,妨礙愛情的是等待。像社區要被拆掉的這陣子阿凱突然打電話來說,有密集的訪調營要辦,周六不能找我了,還不確定下次甚麼時候再來的那種等待。或者後來終於等到電話打來,聲音卻不是他的。電話裡的另一個人說阿凱被抓到警察局去,我趕到現場卻不得不排在記者和公權力之後的那種等待。我想我還愛著阿凱,為此我特別上他們的粉絲專頁上研究他可能變成歷史課本人物的各種照片。看到社區的房子要被怪手拆掉時,他們一夥人不肯走,決心化身土地公把自己綁在房子各個牆柱上的姿勢。「這難道不是妨礙公務?」新聞台上官員在鏡頭前露出猿猴樣的嘴臉,不得不令我厭惡。我平常並不隨便討厭人,但因為抓的是阿凱,使得一切都有了差異。
我趕去城南,已經有其他人提前把他保出來。已經是第三次了,阿凱再一次遍體鱗傷,T恤都是土石。他的語氣急促,不像平常講話的模樣。因為旁邊照例圍了一群人,我只好在一旁耐心等候。
「你沒受傷吧?」好不容易終於有打岔的機會,我趕忙上前問。一個一米七的人,聽到這句話突然被引爆,跟著身上的土石一同崩塌在我的肩膀。「好了好了,我們去吃晚餐好嗎?」我拍拍他的背,順便把他的皺衣服撫平。「不要,吃不下。」「騙人。」「我的胃也一樣離家出走了。」「胃只要聞到好食物即使十萬里路也會返家。」「能煮出那樣食物的店都被拆掉了。」他心有不甘的大吐苦水。
說是這麼說,最終還是可以找到一間這樣的店,麵疙瘩或者蔬菜拉麵,店面雖小但特別溫暖,排場也不豪奢,可以給落魄者如阿凱一種避難所式的撫慰。我看著他大口大口的吃麵,也想著該如何好好跟他談談自己。明明不在一起的時候總是想到很多話可以講,真正碰頭了,靈光乍現的話語卻好像生鏽長垢,卡在喉頭出不來。
「畫畫的那個小屋啊,妳還去找他嗎?」阿凱先主動開口。
「嗯。他最近發生意外了,在早餐街那裏被流氓打,有可能傷到神經。我想要明天再去看他。」
「對他這麼好,他會喜歡你噢。」阿凱眼睛突然銳利地閃了一下,偷走我一根麵條,「還是妳喜歡他?」我不作聲,安靜喝著湯。「妳真的喜歡他啊!」
「兩位的小菜噢!」老闆宏亮的聲音插進來,放上一盤切好的滷味。
「我又沒有這樣說!」我小聲地埋怨。
「那就是喜歡了。」真是令人受不了的傢伙。「對,反正你最近也不太來找我。我為什麼不能喜歡一個更支持我的人?」我圓著眼睛瞪他,生鏽的字詞竟然輕輕鬆鬆就脫口而出了。阿凱停止吃麵,放下筷子。「小姐,你真的要跟我算帳,那為什麼妳就不一起來幫忙社區的事?」
「我說過──我支持你,但我不喜歡把自己放進抗爭的場景。」
「這不是喜不喜歡的問題!妳以為我就喜歡孤立無援的跟怪手對抗,讓成績擺著爛嗎?」
「你很樂在其中啊。」
「靠,我很樂在其中!妳憑甚麼像那些鄉民每天閒閒沒事,吃飽喝足就上網亂說我在做秀?做給誰看?我以後工作面試就會比較順利嗎?妳到底還有沒有社會良心?」碗還有一半的重量,我不想和他吵,連湯沒喝完就先離開了。我很喜歡那家麵店,一點也不希望在裡面爭執。有很多事我還沒思考徹底,一句話就能搞砸全部。我的意思不是說阿凱在作秀,我只是想強調他的確是心甘情願地投入啊。如果不是因為追求快樂,為什麼要放棄一切那麼努力呢?難道說樂在其中也錯了?但我知道,阿凱原來也跟我一樣在等待,只是方向不同。他在等待我變得跟他一樣,擺脫對社會不聞不問的習性覺醒成新時代社會青年。我卻等待他回到我們十七八歲的日子,明明也住在城市的兩頭,想讀的科系更不相同,卻可以每天掏心掏肺的聊天不吵架。那時他住在城的東邊我住在西邊,一整天經過考試的浩劫,只要揮揮手回到我們各自的小屋,所有散失的湯湯水水又會慢慢填補回來。他說他最喜歡一回到家就窩進浴室,卸下衣物然後盡情在蓮蓬頭下排尿,緊接著沖水驅趕、淡化濁黃的自己。我問十七歲的阿凱,你的尿是甚麼味道?他說就像海鮮店隔了一夜的餿水。當時連這種話題都可以聊好久。每天睡前的聊天就像回家,如一個循環的游泳池每天拉開水塞,注入源源不絕的消毒水。等待新的一天又開張,汙染,再關門,再清理。
-4-
回宿舍的路上我跑啊跑的,雨下得很大我卻忘了帶傘。像山洪那樣豐沛的水從前方沖刷下來,從鞋子濕進襪子裡。我討厭禮拜天,宜香自助餐、餛飩麵跟飯捲都休息,我被迫得吃義大利麵或連鎖早餐店。我討厭禮拜天,半棟宿舍的人都回家、圖書館五點關門、全聯的所有葉菜肉類都是我煮不完的四人分。我不想回到宿舍,只能做城市孤兒,上咖啡廳、搭捷運、從夜市的一頭騎車騎到另一頭,想到阿凱某次跟著遊行隊伍對著立法院前罵「不事生產的廢物」,我自覺也應該是他批鬥的對象。我愛阿凱嗎?他其實對我很好,為何我們老是吵架?我尤其討厭這個禮拜天,小屋第一次對我發脾氣,使我也跟著厭煩自己偽善、失根、無所適從的模樣。
小屋少了一隻手,任誰都會生氣的。我到醫院看他,他整個人發黃而且浮腫。來之前我並不知道狀況這麼差,還為他帶了可以畫圖的紙張。真的見到人,我也傻了,只能呆坐在病床旁邊,好不容易擠出一句:「不要想著這件事,你的左手一樣能畫圖啊。」講這句話是不是又錯了?他的情緒更加躁動,「我竟然停下來想跟他道歉!可惡,他憑甚麼毀滅我的手!我不畫了,我本來就畫不好,風景畫人物畫早就過時了。其實我充其量是個畫匠……。」
「風景畫才沒有過時不過時的問題,我不是一直很喜歡嗎?」我想安慰他,又不敢看他。
「可是我不只是想讓妳喜歡!妳的生活……對不起,妳的生活太容易了,很容易被滿足,甚麼都可以喜歡。妳知道跟妳同年紀的學生都在想甚麼嗎?在想著自己要如何被那些坐在金字塔尖端的人雇用,在想著如何讓自己擠進現實的框架,把樂善好施的聖誕老公公留給童年……。」小屋蓬頭垢面的坐在床上,用殘破的啞嗓子說話。我試著辯駁,整個人卻被他的句子拉扯開來變得有點恍惚,想起了阿凱,想起他們相像的部分。「你變好多。」像下雪一樣,我輕輕飄下這句話。
「早應該變。」他不甘示弱。
「早應該像妳聰明讀了醫學系下半輩子不愁吃穿,有那麼多的大學時光可以蹉跎。早應該看清楚不要去抵抗,畫山水跟畫汽車廣告都一樣,根本沒有甚麼自然比人高尚的道理,事實是農安街鋪了柏油路也好、政府要開放自由經濟區也好,就像獅子吃掉羊,人類也只是自然弱肉強食的一環。」
「不是這樣的!」我的腦袋被纏成好幾團毛線球,卻仍然可以清楚感覺到他的思維故障了。
「幫你治療手的人是醫師,為你送水彩鼓勵你好起來的人未來也是醫師。我也有那麼多困難、要準備那麼多功課、那麼多書要讀……,我真的就是比較聰明的既得利益者?」小屋不知道我喜歡他。或者他知道,只是試著拒我於千里之外。「畫畫明明就是你擅長,也是你喜歡的事。你要武裝,你要變成獅子,那我告訴你,畫畫就是你的武裝!」凳子被我踢翻。我在他的床前像一根燃燒的木頭拄著,雙腳隨著他如炬的目光逐漸搖晃至潰散。他終於放棄盯著我,把頭曚進被子,發出如外太空傳來的電波聲浪,每個字都疏離不帶感情,「藝術是最廉價的武裝,像羊的毛長給自己取暖的。」我感覺他也許在哭,但又不敢確定。他已經在這家醫院待太久,被生老病死的奧義侵蝕成一頭野獸了。野獸也是會哭的嗎?我現在真的甚麼都不知道了。
-5-
回到房間,我只開了門口的燈就全身溼淋淋的癱在椅子上。一百種念頭穿過我、粉碎我。才兩天的光景,阿凱再次從警局出來跟我吵架,小屋則少了一隻手。而我甚麼都不是,既未受傷也未真的被誰拋棄,只是自始自終未曾搞懂我們之間的折曲。平常這個時候我早就拉開窗簾,倒到床上欣賞夜景了。但我讓房間鎖著、窗戶關著、窗簾拉著。小屋的畫留在桌子各處,照不到光的時候看起來就像媽媽年輕時代沖洗的黑白相片。指針在鐘面上反覆、單調的轉。我以為我將一直聽到時間流逝直到睡去,沒想到一個鍋蓋被踢翻,「鏗啷」,史多邁竟偷偷爬了出來。「不要跑!」我不由得大吼,聽見我的聲音被門用力反彈回來。
鍋蓋仍在顫抖,持續挑戰我的極限。「你不准離開!」我失態的用破了的嗓子吼叫。平常我是不會對史多邁生氣的,但這一個晚上我有奇怪的堅持,希望整個房間維持在我根本沒回來的狀態。誰都不准干擾我的癡心妄想。總覺得只要這樣持之以恆的戰鬥下去,靈魂將因無處可棲而飄回故鄉的土壤,或者穿越到四五年前的時空。我也一度做出其他假設,如果手機響起來,阿凱也好、小屋也好甚至假如我的房間輕聲問候我能不能為它開盞燈,我都願意把思緒再聚攏到現實的生活裡。但我再努力地不想只被自己需要,卻也必須可憐兮兮地被自己的器官反覆打擾。「卡」,有電鍋被插上,史多邁瑟縮著身子小心翼翼拿起鍋蓋把自己埋起來。更多的器官跟進。午夜十二點,我的臉不再淌淚,取而代之的是廁所的水槽傳來一陣一陣的嘔吐聲,淚腺趴在那裏虛弱的喘氣。「你們害我變得很沒用,知道嗎?」我對著房間的對角線大吼,凍結空氣。指針滑過兩點,松果腺即使再恐懼也按捺不住地爬出來向我告別,像花生那麼瘦小且充滿皺褶的它關了門口的燈,跟肝臟一同爬上樓梯躲進被子打呼。我感覺到很多部分的自己散佈在房間各處,心臟、腎臟、膽囊……。小屋錯了,他們哪一個都不是我所能掌握的。我稍微翻個身,發現因為內臟們傾倒而出,身體竟然輕如薄翼。算了吧,既然他們把房間弄得亂七八糟,我也沒甚麼好假裝的了。
我走到窗邊,緩緩把窗簾拉起,看見整座城市在暴雨中搖曳。所有的燈光、還醒著的眼眸還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店面都和我共同見證這一幕。見證凡是赤裸裸、不穿戴鋼甲建築的都將被大雨洗刷,忍受一整個晚上的寒冷,一整晚的失眠。相較之下,我也許是幸福的。──你看,阿凱是不可能幸福的,除非人民一夕覺醒,把國家改造成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你再看,小屋也是不可能幸福的,除非他的手能用最新科技接回去,回到從前的揮灑自如。他們此刻也醒著嗎?會不會也亮出像海上燈塔那樣的瞳孔,把我無光的靈魂接回家?還是我的幸福是其他的,像早餐街那樣知足常樂,如何汰換更新也不曾埋怨,白天認真排放油煙廢水、晚上則認分的聽引擎聲好好入眠……。想到這裡,想到我的內裡不斷出走,身體如今空洞得像可以被雨絲直接穿過去,那就對了,或許我的幸福只不過是渴望變成一朵雲,漂浮在城市的上空欣賞各種夜景,想要消失的時候就被吹散、想哭的時候就降下連日的大雨。
阿凱、小屋,你們是山,夜半時起一場大霧,我們就在地表和天空的兩頭迷失摸不著彼此的形影。你們都說陽光總會出現,會大方的照在我們身上。於是我等待,無法預知終點的等待。以為自己可以撐過黎明,卻還是在凌晨四點鐘的時候沉沉睡去。同時,早餐街兩側的鐵捲門,一張一張被拉開。
——————————————————-
王:這篇小說是我心中的第一名,沒有領先很多,但也算領先一大步,已經是很有專業水準可以出書的文筆,情緒也很具有衝擊性,但描寫的細膩程度更勝荒城,胃掉出來喜歡躲在電鍋,這個人一定常常用電鍋煮飯而且忘記插插頭,我也常常做這種蠢事,這種荒謬寫法但看起來不突兀,因為年輕人在衝撞這事件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會讀起來稀奇。這篇小說意識形態超不正確,很有生命力的青春成長小說,主角們個性很奇怪,但情節不會淪為胡說八道,有高度控制力才能寫出這種火侯。
藍:是我評價最高的作品,短篇小說具備的條件都有,很快讓人眼睛一亮,題材也很棒,可是並沒有領先其他作品太多,其他兩位老師講了很多優點,來補充一下這篇的缺點,象徵性的東西太早被看破,本來很期待胃的出現,活靈活現,但最後只是象徵物讓人有失落感,有種感情被作者欺騙的感覺,胃掉出來不需要合理化,應該要發揮作用,最後竟然沒什麼影響,沒有特別意義存在,但整體而言整篇都是很優秀的作品,相信作者在未來也很有發展潛力。
吳:非常欣賞這篇,用胃當比喻很有意思,人物也很熱血,讀起來有冷冷的成長和悲傷,對有人對現實的堅持和幻滅,對現實妥協,用早餐街當題目也很有隱喻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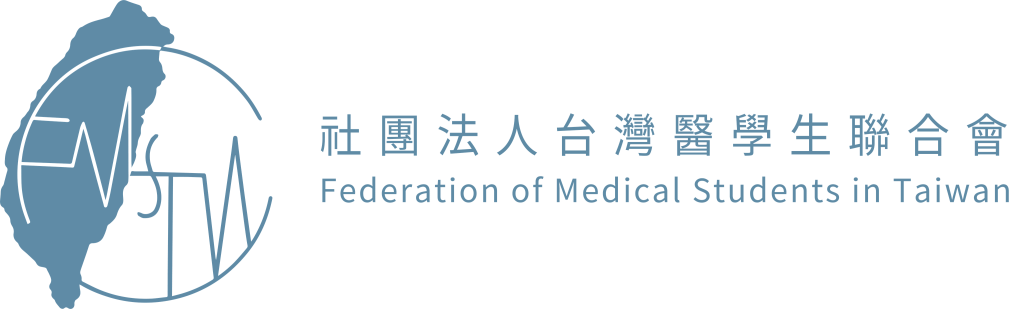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