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屆散文組佳作]飲冰室信徒《誰的帽子》
1 :30AM。
距離午夜十二點,距離我們成為「好哥們」,已經過了一個小時,又三十分鐘⋯⋯。
依稀,夕日灑落海面成一片金粉閃閃爍爍,粼粼波光輕巧地,踏著浪,一陣陣淘洗妳腳下的來自浪花彼端的沙粒,把它們挑回海中重新洗淨,再送回妳的身邊。妳扶著帽簷,好像怕一個不小心,那頂帽子會悄悄遛出妳盪漾的笑容之外,不再回頭。妳一襲白色連身衣裳,搭配那頂被陽光過度曝曬過後而呈現,燒焦的,褐色的寬邊草帽──是編帽子的師傅一條藺草一條藺草細心編出來的吧!腳踏著斜斜的四十五度,妳沿著海水與沙灘的交界處,小心翼翼踏出每一個步伐,默數著回到海中的白沙⋯⋯。
柔和光線勾勒出妳側臉,我靜靜在一旁欣賞,微笑著。一陣風突然使了點力氣,還是搶走了妳頭上那頂帽子,帽子飛呀飛的⋯⋯,我向上一躍,以為接到了,那頂帽子⋯⋯
然後,我醒了。1 :30AM。
「王爾德說過:『男人和女人之間,不可能有純友誼的存在。』妳覺得呢?」我問道。
「什麼?」妳稍稍抬起目光望向我,微蹙著眉,右手無意識地用筷子撥弄著盤中太多的胡蘿蔔絲。
「男女之間可能有純友誼嗎?」我重複自己的問句。
妳直起身子,像是做了個重大的決定,笑著跟我說:「當然有!」
走出店門口,才發現大雨傾盆,嘩啦啦把街道本該擁有的聲響通通掩去,我沒帶傘,和妳之間只有一把傘的距離。妳未曾留意,我那受雨打風吹的右半身,淋個濕透──我原本以為,我們不會成為純友誼。
對妳的初次印象,還停留在某次課堂報告上,妳說著死前想做的幾件事,依稀記得其中的一件是:找到懂妳的那個人。那時的妳,沒激起我心底太大的漣漪,彼此之間也說不上幾句話。真正認識妳,比較熟了就要等到半年後某次因緣際會下的一頓飯。那頓飯,我和室友竭盡所能聒噪不休,玩遍把戲,祇為別讓氣氛尷尬,誰叫我們是臨時起意約妳吃飯?妳多數時間只是靜靜聽著,偶爾一兩個問題,卻都足以讓空氣晶瑩剔透了。
妳彈鋼琴,我只見過幾次。
妳把專注寄放在音符之間,彷彿凝結了四周,卻持續輸出妳對五線譜間每一個黑色豆芽懸掛位置的仔細解讀,流瀉出滿溢的情感,卻隱隱然不喧賓奪主,用妳的指尖,起落出一個神聖界線。同樣是黑白鍵起落,樂曲的風采,卻如此不同於他人。
我每次走在無瑕的沙灘上,走到那個習慣的位置,等待那個即將到來的時刻──妳會緩步從沙灘的另外一頭走來。我曾對妳說過,一襲白裙,一頂帽子,真好看!妳笑著對我說,那和某個妳喜愛的卡通:銀魂──總是傳遞著盡全力守護得來不易的幸福,這樣一個訊息──的女主角同一個樣子。妳深邃的眼眸,藏有太多如海深的秘密,我知道我無法潛入,偶一在海面上激起的波紋,也馬上受浪花本身淹沒,終究留不著些許痕跡。於是夢裡,我買了那頂帽子給妳,寄出幾張明信片,把腦中鍛造的想像作為筆尖墨水化身成為文字,文字宛若我的音符,流瀉紙上,盡力篩去過多的情感,呈現最純淨潔亮的幾筆。
夢中的妳收下了那頂,那頂編藏了有我的名字的帽子──然後,我醒了過來。
他拉小提琴,班上同學,和妳同為鋼琴社社員。因著社團迎新準備的需要,你們倆總是合奏一首曲子,並在練習一整天後,相偕去看場電影。我在心中描摹你們兩人走在一起的背影,輕輕地消去過多的光線,讓目光聚焦,那是一幅多麼和諧的畫面啊!那麼,我該再多做努力嗎?所以當我鼓起勇氣時,想再問妳能否一起吃頓飯時。妳面對我的邀約語帶遲疑,因為時間剛好和妳跟他約好的時段衝突,我心中一愣,鎮靜地,若無其事地,結束話題掛上電話。我一個人,漫無目的徘徊在書店,手上多增加些書的重量,用來換取內心下沉失衡的天平可以再次回到原本的樣子。機械式走向結帳處。看著店員的嘴形得出價格。
「啊,好像買過了頭。」我一邊拿出鈔票,一邊掏出自己的心情。
妳幾次到海灘邊散步,戴著我送的那頂帽子,我就以為我是越來越接近妳了。我們幾次談到過去,妳說起那好像已經遺忘但猛然間想起仍會隱隱作痛的傷痕,兩行清澈的溪流還是不爭氣地,從看似已經沉靜的深潭汩汩流出。而這些時候,我只能道聲歉,挑出一、兩首歌,幾段話聊以安慰,只能指向海天連線處,笑著說即便是濃得化不開的黑夜,也會有星子陪伴著妳!收起眼淚吧!漫漫長夜,我以為我會陪妳度過,可當下一個旭日露臉,我只是如夢初醒。
到宜蘭,妳的家鄉,參加營隊。玩笑式地打電話約妳在營隊結束後,台北碰個面。不巧,再一次撞上妳和他相處的時間,電話這頭的我,就好像看見妳的眼神游移不定,努力想要找個好方法婉拒。我感覺到了,不為難妳,電波這頭,我努力將多餘紛雜的情緒萃取成片段話語,只是好像有些東西,難以聚集成形,成了細細粉末,消散空中⋯⋯。記得我曾問過妳,是否仍未走出那段沉痛,還是已經準備好接受下一段情感?那次妳淺笑不語。而這次,妳說出口了。
「其實新的一段已經開始,只是一直找不知道要用什麼方式說明⋯⋯。但,還是要跟你解釋清楚,我是相信有純友誼存在,所以,才會是你的朋友噢,我一直把你當好哥們⋯⋯」
妳電話那頭的聲音開始嗡嗡作響,轟得我腦中一片空白,全然的神經短路衝擊著我,導致我的笑聲僵硬在話筒裡,仍舊勉力笑著──妳沒察覺,又或者妳知道了,只是默契地不動聲色。我努力在最短時間內修復幾條神經,發出語焉不詳的詞句以維持兩人間的熱度⋯⋯。
掛上電話,曾經擁有的,那些間斷的笑聲,依稀迴盪在耳旁。
妳和他攜手走來,平日明亮的沙灘顯得愈發光彩。我急忙找了個礁岩隱匿了蹤跡,躲進不明顯的角落。抹去那些腳印,一如我努力消去這些夢境。
我失眠了。
夜很深,吸入太多沈重,也意外地殺光我的瞌睡蟲。夜風吹動營隊手冊,一方面擔心隔天的課程,一方面溫習內心的殘敗,無意尋找睡眠,深怕其伴隨的夢境太過無情。時間滴答放大,讀著夜的秒數:一秒、兩秒⋯⋯三點、四點,依靠著手機螢幕,磷磷微光映照著一張憔悴的臉龐,氾濫地寄出一封又一封的簡訊,給遠方已然在夢的國度裡逡巡的友人,頑固地將情緒推開。翻來覆去輾轉反側仍舊無眠,我下床,拿起筆,就著紙面,讓未經雕琢的文字吞噬了心上的空白,並渴盼著,渴盼著溫柔的回應。是麻木,或是傷心太多,滿溢眼眶後,眼皮就再難以闔上。妳說怕傷了人,但仍把話說清了。我勢必得退出妳所畫的那條線外,最後還是接受了由妳親自加冕的,名為純友誼的荊棘王冠。⋯⋯然後,彷彿看見妳的身影,向我道了聲謝謝,以妳一貫清新不失俏皮的優雅。
我再也回不去那片海灘了。想大叫,一路狂奔,在夜的邊界聲嘶力竭。或者是走到另外一片海,聽浪聲反覆拍打空心的礁岩,又或許喝了爛透更合適,至少能把滿腹愁腸都嘔出來下酒。可所有方法都是死路,因為我終究只能固守一方死硬的床板,奮力尋覓切斷五感的方法。血絲緩緩步上眼白,胸口某部分細不可聞的裂縫不斷綻放的聲響,成了黑夜唯一伴奏。
妳和他早已在一起一段時間了。原來我知道得已經晚了。
找不到適合的歌曲可以熨平心上的摺痕,淚腺退化,我只好在情緒的大沙漠中乾涸,沒有綠洲,連海市蜃樓也消滅了蹤影。再一個小時就要天亮了,半夢半醒間我成了方格的囚徒,提起筆,卻無力篆刻深刻的文字進紙面,只能留下些膚淺的字句。我告訴自己,這是一場儀式,藉由迅速記下狂雜飛舞的情緒,再之後進一步好好沈澱,我就能從有妳的世界離開,重新回到曾遺落的自己身邊。
獨自迷亂在那熟悉的海岸,燈塔亮了,一閃一眨。我向海中走去,像受到什麼東西吸引,走向那被切割成一塊塊,填滿不同顏色的海洋,碧綠色、深藍色以及許多。我挑了最乾淨的那股流動,吸收最多色光所以帶有最深沉色澤的那道水。隨鹽味進入口中,我游離那個岸,游離那個每每駐足停留等待期盼的位置,背向那片陸地,消失在這片海裡。渴盼泅過最遙遠的距離,又或者,放肆沈入海洋這廣袤的荒疏之中。
天亮了,晨曦無聲息暖醒大地。山坡上的林子愈發翠綠,隨風搖擺著,鳥鳴興高采烈,爭相奏出一天的新曲,而我拖著一身的疲憊。支撐過了營期,肩上的行囊沉甸甸。調整好新的姿態,為的是重新面對短期之內編織在妳、我、他之間錯綜複雜帶著尷尬的網。回程的車子誤點了,因此逗留在宜蘭,更多一點的時間。視網膜底不斷進行記錄,亦或是消去。短期之內,我不會再來宜蘭這個地方了吧!不論是真正踏上這塊土地,或者是午夜夢迴時刻的流連。即便這個地方洋溢著無限的美好,美好的讓人目眩。誤點車子進站,窗子切割出快速流動,高速曝光底片般的風景,向著後方競相追逐遠去。因為車子誤點這意料之外的事情,留在宜蘭的時間,終究,是久了一點。
我離開宜蘭,我走開了。至於思慕這地方的那個我,則跟著深夜裡所寫下的線條,留下了。「我是因為相信這世界上有純友誼的存在,所以才會是你的好朋友噢!」我把妳說過的這句話珍藏起來,對折再對折後縫在心的最深處。也許有一天,我真的會去買一頂手編作而成的帽子,送給妳──以好朋友的身份。
「盡全力守護得來不易的幸福吧!」我打在寄給妳的簡訊中。想起妳喜歡的那部卡通,於是留下這樣一句話。
月兒彎彎高掛天空時,睡夢之中,我又依稀看見,那沙灘有妳。而風吹落了──原本屬於我,後來屬於妳,最後不屬於任何人的,那頂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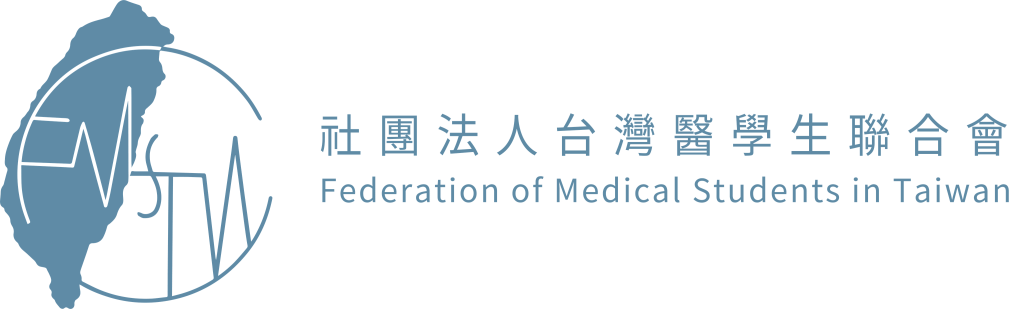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