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小說組佳作]高醫後醫一-張雲翔《門》
來了,來了,人們聚在陳家三合院外頭,鞭炮聲響了,幾個穿著拖鞋的小孩努力墊起腳尖,迎娶的三輪車隊很長,上頭載著一箱箱嫁妝,還有那個隔壁村來的新娘。
三合院的大門打了開,走第一個進來的是媒人。
「人未到,緣先到,入大廳,得人緣。」
把頭髮染得烏黑的中年婦女邊撒著鉛粉邊唸。
「緣錢粉撒呼澎澎英,金銀財寶歸厝間! 緣錢撒高高,新娘生子做狀元!」
家裡公婆姑嫂暫時迴避了,陳家一位她從未見過的長輩迎向她,將竹篩放在她頭上,領她進門。
「來!來!踩這裡!右腳先!破瓦無破人,破外無破內,新娘入門攏無破!」媒人在一旁說,她的腳踏出,隨即聽見地上瓦片的碎裂聲。
「跨火爐喔!」
她輕輕提起裙子,跨過地上的那團火。
陳文斌,乾造x年x月x日時建生。
李秋華,坤造o年o月o日時瑞生。
「八字真的是很合!算命的說,他第一次看見這麼合的!旺夫家!子孫都事業有成!我那時候二話不說就定下來了!」陳文信的母親笑呵呵的看著她跨過一個又一個的儀式,慢慢走進這個家成為她的媳婦。
已是陳李秋華的女子低著頭瞥了眼丈夫發亮的皮鞋,視線又落到正廳的地板,望見那門檻,還有遠處那只剩餘燼的火爐,嘴角忍不住偷偷升起一道微笑。
宴客完畢後,她捧著甜茶,媒人在旁喊著「新娘出大廳,錢銀滿大廳」又再進入廳堂。
「來,來,食新娘茶。」長輩招呼,賓客接受她的奉茶。
「食恁一支菸,互恁尪某年年春; 食恁一杯茶,互恁年底生雙個!」
「手牽手,天長地久; 喙抵喙,萬年富貴。」
長輩開心的說著吉祥話。
「請喝茶。」她彎下身,將茶杯遞到一個皺著眉盯著她的長輩面前。
長輩嚴肅的雙手抱胸,雙眼直瞪著她。
「請喝茶……」他生氣了?緊張與不安的情緒向她襲來,她做錯了什麼?
「妳賣鬧啦!真的知道我是誰嗎?」一頭白髮的長輩站起身來,指著她激動大罵,她後退兩步。
他手一揮,她的茶盤掉落在地,冰糖、蜜餞撒至空中。
他的面容哀傷又蒼老,柔聲的說:
「我是阿斌,妳想起來了沒有?五十多年前娶妳的那個阿斌啦!」
「實在是很抱歉!不好意思造成各位的困擾……」
陳文斌的二兒子瑞昇在病房外向護理人員鞠躬。
「叔叔沒關係啦,地板我們清就行,你多去陪陪阿公讓他心情好一點!」年輕的護理師跟瑞昇的獨生女差不多年紀,看著她拿著抹布急急忙忙的入內清理,讓他對爸爸的失態感到萬分慚愧。
「爸也真是的,這麼大聲做什麼?媽是被他罵一罵就會好了嗎?唉……打通了沒?」他問身旁的妻子。
瑞昇與妻子都在同一所國中任教,瑞昇今年剛升上訓導主任,女兒小文在校內功課也不錯,此時小文正在走道上的椅子上專心看書。
妻子搖頭:「你大哥還是不想來。」
「唉…..爸這樣,媽這樣,他也這樣…..這個家…..」
急促的腳步聲打亂他的思緒,一個戴著墨鏡,一襲大紅洋裝的女子踩著高跟鞋快步走來,後頭跟著一個頭髮半金半藍的少女,她誇張的髮型讓小文的注意力離開書本,抬起頭直盯著瞧。
「媽的情況如何?我等下三點跟朋友有約,還得趕過去,太多年沒回來這裡了,太多要見的人。」她撥了又撥黑色的大捲髮,充滿笑意的看著陳瑞昇。
「陳瑞慈,妳夠了沒?妳這趟回來的目的是什麼?朋友比媽還要重要嗎?妳急急忙忙地來,又要匆匆忙忙地走嗎?到底有沒有為人子女的心啊?」
陳瑞慈摘掉墨鏡,對著二哥不悅地說:「不然你要我留在這邊給你們嫌喔?都被嫌多少年了?太妹啦,混幫派啦,你跟媽不是一直覺得我很丟家裡的臉?那我現在滾到美國去不是很好嗎?省得礙眼!」
「好啦好啦!」妻子緩頰:「瑞慈難得回來,就少說她兩句。」
陳瑞昇看看妹妹身後低頭的女孩,問道:「這妳女兒喔?幾歲了?」
「十四啦,我就是懷她之後去美國的,你忘囉?她跟小文同年。」
「她爸爸呢?」
「分了。」
「妳離婚?」
陳瑞慈不願回答,踩著高跟鞋叩叩叩的拉著女兒進入病房。
「爸!」
她將女兒往前推一步:「來,Kelly,叫阿公。」
女孩心不甘情不願的小聲吐出阿公兩個字。
「妳回來喔,還帶個小的。」父親面容僵硬的駝背坐在病床旁的椅子上,看起來比瑞慈印象中更瘦更矮。
病床上,是一個眼神呆滯,直望著窗外遠方某處的母親。
瑞慈看著她不發一語。
「她什麼都忘了啦!連妳跟她吵架然後離家出走都忘了啦!」父親搖搖頭。
「啊妳大哥呢?」父親繼續問。
「阿龍!阿龍!你在哪裡?」床上的母親突然驚慌失措起來,像在做夢一樣,眼睛卻睜得老大:「有沒有人看到我的阿龍?」
「阿龍好好的,在中部當乩童啊,妳不要慌,不要慌…..」陳文斌拍拍陳李秋華的背,像在安撫孩子一樣。
「兒孫自有兒孫福啦!」
「哥,你跟我提的那件事呢?」醫院大門口,陳瑞慈拿出打火機點菸。
「妳回來其實是因為這件事吧?」陳瑞昇點點頭:「唉,也對啦,市值三千多萬……我看哥也遲早會跟我們聯絡啦!他應該也要錢吧?」
自從瑞慈隨著一個男人私奔到美國後,兩人事實上已經多年沒聯絡。陳李秋華過去幾年頭腦還清醒的時候,一提到這個從小到大不停惹事的頭痛女兒,總是唉聲嘆氣的直說造孽。
不過她從未提過她的長子陳瑞龍。
嫁來陳家多年後,陳李秋華成了個作風強勢的母親,這樣的母親碰巧又生了個極有主見的調皮兒子。老師說,陳瑞龍是班上數一數二聰明的,論懶惰也是前幾名,他不是笨,只是不念書-這個評語讓陳瑞龍十分得意。
十幾歲的時候,瑞龍便不停翹課翹家,和群朋友整天鬼混,有天決定去遠親那學當乩童就不回家了,之後幾年陸續寫簡單的信回家,一封是說自己結婚了,一封是說跟人合開了一個神壇,生了一個兒子。
不回家的大兒子和女兒總是讓夫妻倆心寒,唯一能安慰他們的是考上師專,後來又順利取得教職,成家立業又孝順的二兒子瑞昇。
這次陳瑞慈會回來,除了瑞昇擔心母親的失智症極速惡化外,還有另一個理由:他們的老家即將面臨都市更新。
陳瑞慈抽著菸問:「你是說,建商要我們二選一嗎?原地新建的房子或三千五百萬?不是我在說,我們家那種老三合院在那種鄉下能有機會都更,跟中樂透一樣。」
「爸反對,想留老家。」
「你呢?」
看得出來陳瑞昇很猶豫,這是他人生中少數違背父親的時刻。
「我是……比較想換錢啦,畢竟我之後打算送小文出國唸書……就還在說服他。妳呢?」
「當然是錢啊,我和Kelly還要過生活,我離婚贍養費可沒多少。」
「我有傳簡訊給哥了,有跟他說媽的病,也有說這件事。」
兩人在醫院門口說著這件事的同時,陳李秋華的病房正快步走進幾個醫護人員。
「打鎮定劑!先生不要驚慌,我們幫她打鎮定劑了!」
「怎麼會這樣?你說啊,我老婆本來好好的,怎麼變這樣?」
年輕的醫師對陳文斌說:「陳先生,情緒激動和妄想是失智症的其中一個表現,所以陳太太有時的確會這樣。」
「我中了,我中了……換房子了……買新房了…..」床上,陳李秋滿的意識因為鎮定劑逐漸喪失,她不停小聲喃喃自語著。
「醫生,這不是妄想啦,是真的。」陳文斌說。
那是民國五零年代的夏天。
陳李秋滿跪在陳家的正廳牌位前。此時的她已經不用張開眼偷看,就知道走幾步就會到達正廳的門檻,知道三合院大門的方向,知道陳家的一磚一瓦哪塊剝落,哪塊不急著修。
她虔誠的照三餐跪,希望陳家的祖先能顯個靈,報她幾個明牌。
「零到九十九啦,給我幾個就好。」
「阿母,妳在拜拜喔?」陳瑞龍站在門檻上問。
「下來啦!那邊不能站啦!」
陳瑞龍蹦的一聲重重跳下來,讓祖先牌位也震了一下。
「是那個大家樂喔?祖先真的知道明天會開幾號嗎?」
「當然!要誠心誠意的知道嗎?不可以對祖先不敬!不然打死你!」
陳瑞龍做了個鬼臉,陳李秋滿怒火中燒,追著他打,兩人在神像前你追我跑好一番,忽然陳瑞龍倒在地上大哭起來,指指正廳的門檻。
「你看,有報應吧?摔倒了啦!」
「阿母,簽05 13 16 24 31跟51。」陳瑞龍突然收起哭臉嚴肅地說。
「啊?」
「剛剛倒在地上有聲音跟我說的。」
「真的?」
陳李秋滿雙手合十朝祖先一拜,然後用力抱住兒子。
陳瑞龍出生後幾天,她特地找人算了八字,算命的笑笑對她說:「妳這個兒子喔,神明和祖先都很疼啦!有很多福氣,不用你煩惱!」
「你沒受傷比較重要啦!」她將兒子摟在懷裡。
「我中了!我中了!買新房子了!」
第二天,陳李秋滿從三合院大門狂奔進來,興沖沖的召集一家老小。
她把陳瑞龍抱在懷裡:「你看祖先疼你疼成什麼樣!」陳瑞龍在他懷裡咯咯笑著。
神秘的是,在那之後無論怎麼簽,中獎都跟她無緣了。
煙薰的騎樓外停的機車染上一層灰,小小的一樓店面門口擠滿了跪拜的人,誦經聲讓星期天上午整條街還在睡的人們不得不清醒,今天是這個小小宮廟「天霞宮」的法會,人們對裡頭的神像跪了又拜,拜了又跪。
來了,來了,人們聚在騎樓窺探裡頭的情形,幾個穿著拖鞋買早餐的人努力墊起腳尖看熱鬧,起駕了,他們有點興奮卻不敢表現太明顯,只能低聲地互相告訴彼此。
乩童胸前圍著八卦兜,下身圍著龍虎裙,彎著身閉著眼,一手扶桌,頭搖得越來越快,整個人抖了起來,然後扶桌的那隻手開始用力拍打桌子,一腳跟著用力跺地,整張臉因為用力而扭曲。
站在一旁的桌頭說道:「太子爺駕到,弟子有何事趕緊稟報上來!」
一個中年男信徒恭敬的敬禮:「弟子高天成想問媽媽的病怎樣才會好。」
乩童喃喃自語,雙手朝天快速揮打了幾下,然後拿起桌上的毛筆龍飛鳳舞的寫了幾個草字。
桌頭看了一眼,微笑對高先生說:「太子爺要你不要煩惱,媽媽的病到明年立春就會有轉機,在這段期間你要多做善事,存善念,轉機就會來的比較快。祂還要告訴你,人的命天都註定好好的,只要平常多做有福德的事,就會把你的命改到好的方向啦!」
高先生聽了,滿目的愁容頓時放鬆:「多謝太子爺!多謝太子爺!」
一樓的神廳後方有個小門,門通往陳瑞龍家的客廳。
電視上放著豬哥亮的綜藝節目「豬氏會社」,陳瑞龍坐在電視前的凳子上,穿著汗衫,腳上踩著藍白拖,翹著腳,叼著根菸,打開電風扇對著自己直吹,再灌下幾口高粱。
一旁散亂的扔著他擔任乩童的八卦兜、龍虎裙和各式法事用的道具武器,擔任桌頭的阿明師皺著眉走過來。
「欸,阿龍。」阿明師是個瘦小的禿頭男子,平日他總是嘻嘻哈哈,陳瑞龍的老婆秀芬總嫌他不太正經,但此時阿明師的臉相當嚴肅。
「阿龍!我們昨天不是說好了?」
「啊?說什麼?」
「你給我幫幫忙!你昨天不是說今天法事要讓大聖爺上身?怎麼變成太子爺的動作?嚇得我快漏尿了!我武器都準備大聖爺的,幸好信徒沒注意到…..我趕緊改口太子爺駕到…..」
「你不要黑白亂講啦!我們什麼時候說過了?我怎麼沒印象?」
秀芬氣急敗壞地衝過來:「陳瑞龍!你就不能注意一下嗎?瓦斯爐上的湯都要被你燒乾了!你想燒房子啊!你現在又在做什麼?又在喝?不怕死喔?」
幾個月前,重度酒癮的陳瑞龍曾因為肝昏迷住進加護病房,休養了幾個月,好不容易才從鬼門關前走回來。
「怕什麼啦!我是關公的義子欸!命還被關公撿回來過!」
「哎喲!腳起來啦!」秀芬將凳子旁陳瑞龍亂丟的衣物拾入洗衣籃,繼續說道:「每次法事完就只知道喝酒看電視,你兒子呢?那麼晚了還沒回來一點都不緊張喔?還有你弟弟傳給你的簡訊,你回了沒?」
「妳不要一次念我這麼多,什麼簡訊我沒印象啦!」
阿明師看兩人快吵起來,覺得有些尷尬,趕忙說:「阿龍、阿龍嫂,我家裡還有點事,先走。」
「好好好,明天見!大聖爺,我會記得啦!」
阿龍繼續看電視,秀芬機靈的走到門口攔住阿明師。
「阿明,你老實說!阿龍這幾天是不是又去賭?」
「我…..我不是很清楚…..是有去簽樂透和六合彩啦,還有去巷子口打麻將…….其他我真的不知道…..阿嫂…..抱歉啦!」
「盯好他!」秀芬不悅的送客。
「對了阿嫂,有件事我還是提一下好了…..阿龍他,最近是不是跟冠志吵很兇啊?他做法事的時候忘東忘西的,有次更誇張,在離家不到幾百公尺的地方迷路,還很容易生氣欸……不知道在氣什麼。」
「這我都知道!我是他老婆怎麼可能沒發現?還是謝謝你啦!慢走!」
秀芬關上門,當作沒事,對陳瑞龍繼續碎碎念。
時鐘指針來到午夜十二時,秀芬焦急的來回踱步。
接著她總算聽見鑰匙開門的聲音,他們的獨生子陳冠志終於回家了。
正在就讀明星高中的陳冠志穿著學校制服,背著書包,低著頭走進客廳。
「你好歹也打個電話啊!」秀芬指責他。
陳瑞龍醉醺醺地出現在客廳:「很丟臉是不是?家裡做法事讓你家都不想回嘛!我跟你說啦,不管你多有出息,你都是乩童的兒子,我的兒子,跑也跑不掉啦!」
「你講這種話做什麼?」秀芬想控制場面卻拉不住火爆的父子倆。
「我就是覺得很蠢,你是真的乩童就算了,還根本是假的!每天在那邊招搖撞騙還一直喝酒賭博,憑什麼大聲啊!」冠志憤怒回嘴,然後衝回房間用力關上門。
「今天是冠志的生日……」秀芬嘆口氣走回房間。
家裡的走廊熄了燈,只剩瑞龍一人所在的廚房燈是亮的,坐在餐桌前開了瓶啤酒。
冠志周歲生日的那天,瑞龍和秀芬讓一群朋友來到家裡,舉辦抓周的儀式。
「我跟你們說啦!我這個兒子真的是很乖很聰明!」陳瑞龍得意地抱著兒子到朋友面前獻寶:「算命的說,沒看過這麼會讀書的命啦!將來當老師,當醫生或是當律師都難不倒!」
瑞龍幫冠志準備了筆、幾本書、算盤、印章、提款卡等十多項物品,阿明師笑哈哈地問:「怎麼不再放張六合彩跟你問神的七星劍?」
其他友人也起鬨:「對啊,你是關老爺的義子,那他就是關老爺的義孫子!」
「不要啦,這些就夠了。」瑞龍微笑道,悄聲在小孩耳邊說:「阿志,聽爸爸的話,等下去拿那本書喔!」
冠志嘻嘻笑著,不知道他到底聽不聽得懂。
不過最後,他在大人的笑聲當中將書放到懷裡。
聽長輩們說,當年瑞龍周歲的時候,媽媽陳李秋華也在古厝讓他抓周。
當年擺了很多東西,但他最後抓了那兩瓣紅紅的,可以讓人丟來丟去,讓人了解神明想法的小道具,年紀小小的他,對結果出來的瞬間總是充滿驚喜。
「還真的是天公伯疼的命啦!」親戚們將他抱得高高的,陳李秋華笑得合不攏嘴。
陳瑞龍嘆了口氣,將喝完的啤酒空瓶丟入垃圾桶,關上燈回房。
第二天一早,法事繼續,陳瑞龍繼續表演神明上升,眼睛緊閉,頭快速抖動。
「哥,我們一定要學這個嗎?我不想當乩童,想繼續讀書。」
不知為何,腦海中浮現二弟瑞昇十多歲的樣子。
那一年春天,父親陳文斌患了場大病,家裡經濟又因為陳李秋滿簽六合彩欠了一屁股債陷入困境,有個在當乩童的遠親問他們,要不要試著來當助手,說神明會很保佑他們家,也會讓父親的病好轉。
迷信的母親信了這番說法,要三兄妹去那邊做事,其中她逼得最緊的自然是小妹瑞慈。
「女孩子念這麼多書做什麼?反正妳也不太會讀,每天惹事,早早去工作嫁人比較好!」陳李秋滿說。
叛逆的瑞慈激烈反抗,母女衝突越來越多,某天學校訓導主任打電話來,說瑞慈和不良少年混在一起,陳李秋滿回家後給了她一個巴掌,瑞茲便氣得離家出走,偶爾才寫封信回家。
「好啦,我去,你就繼續放心念。」瑞龍拍拍弟弟的肩,看了眼在拜祖先的媽媽,她依舊不死心的在求明牌。
幾天後他整理了一袋行李扛在肩上,走出陳家。
「瑞龍,要認真打拼!注意身體!要常回來喔!」媽媽在身後說。
陳瑞龍沒有回頭理她。
奇蹟的是,陳文斌的病在那不久就好了,陳李秋滿十分興奮,擺了幾桌流水席宴客。
然而瑞龍從此沒有回家,只是和瑞慈一樣按月寄錢來,結婚後甚至還刻意搬去外縣市。
眼睛張開時,他本以為會看見熟悉的神龕,熟悉的桌子,熟悉的法會道具,但在他眼前的是白慘慘的日光燈,身上還穿著醫院病人才會穿的衣服。
眼前的是皺著眉搖頭的阿明師和妻子秀芬擔憂的表情。
阿明師開口:「頭還會不會痛啊?」
「頭?我怎麼會在這裡?」
「我把你的頭按在桌子上啦!不然怎麼辦?嚇死人!」
秀芬突然大哭起來。
陳瑞龍開始緊張:「我……我到底怎麼了?」
據阿明師說,當天法事開始時一切都很正常,然而請神上身的時候陳瑞龍開始不對勁,他又拿起三太子的武器,念三太子的台詞,卻做起大聖爺的動作,這對一個當了乩童三十年左右的人來說十分詭異,阿明師努力配合的向信徒宣稱三太子駕到,然而陳瑞龍的動作和語言越來越離奇,已經超出過去和阿明師一搭一唱的範圍。阿明師看得越來越害怕,心想著:「這次該不會是真的上身?」努力繼續向信徒解釋。
然而陳瑞龍越來越激動,好像是在對空氣說話般胡言亂語,最後開始追打起一個信徒。
「阿龍!阿龍!冷靜啊!」阿明師臉色發白的雙手環抱住陳瑞龍,陳瑞龍不停咬牙切齒掙扎,阿明師大喊:「大聖爺…..三太子……不管是什麼啦,快走吧,求求祢快走!」
最後他將陳瑞龍整個人按壓在神桌上,陳瑞龍似乎氣力放盡,趴在桌上昏了過去。
「是喔……真的上身了。」
一個年輕的醫生拿著一疊資料走了進來,看到他陳瑞龍才回過神自己是在醫院的病床。
「那為什麼要把我送醫?我沒事啦,回家回家!」
「都來了就做個檢查吧…..」阿明師安慰他。
陳瑞龍聽了大笑:「你會怕?真的是很好笑,做桌頭的竟然怕真的起乩!」
看到秀芬焦慮的樣子,陳瑞龍才稍微克制下來。
「陳先生你好,我們這裡有份量表,可以方便你回答一下嗎?」醫生詢問。
廚房的燈亮著,陳瑞龍開著啤酒,對著大樂透彩卷。
「又沒中。」
「乾脆就別買了,我們沒偏財運啦。」秀芬打開抽油煙機,重新加熱晚餐的菜當宵夜。
「冠志睡了吧,妳怎麼不去睡?」
「你今天這樣是要我怎麼睡?」
「好啦,對不起啦,嚇到妳。」他又喝完一罐。
「我是在想啦,跟二弟小妹說一下,我跟爸一樣,不想都更,想留房子。」
「你之前剛看到簡訊,不是還跳起來說我們中大獎了?不是想換錢?」
「畢竟就是個回憶嘛……過年,在三合院大門貼春聯,放鞭炮,大家聚在一起,現在哪有?」
秀芬將菜放到餐桌。
「阿龍,你老實說,你最近是不是也發現自己怪怪的?」
「就跟妳說不要擔心我!今天我只是因為緊張!誰知道那個醫生問那什麼問題,這裡是哪裡,我今年幾歲,一百減七再減七是多少,無聊嘛!這些平常很少講的誰反應會這麼快?我還年輕啊!怎麼可能啦!」
「今天醫生有說啦,報告下星期會出來,他懷疑是什麼…..早發性失智症啦,覺得你太年輕了,機率大概五千分之一。」
瑞龍聽了大笑:「五千分之一,不要開玩笑了,我陳瑞龍什麼都不中,就中這個喔?」
「可能會遺傳。」秀芬的頭低了下來。
「好啦!先去睡啦!想這麼多…..」他把秀芬趕回房間睡覺,隨後自己靠在廚房的牆上看著窗外。
再笨的傢伙也會發現家裡氣氛不尋常。
從上星期開始,父母親就一直跑醫院,兩人晚上幾乎天天吵架,冠志跑去問媽媽,媽媽便掉眼淚的躲回房間,爸爸酗酒的情況比去年更嚴重。
冠志與爸爸自從上次吵架就沒再說話了,兩人各過各的,今日冠志比平常早回家,看見陳瑞龍翹著腳在客廳看電視。
「你來一下啦,我有話要問你。」
「什麼事?」他做好被罵的準備了。
「什麼是基因啊?」
「啊?基因?」冠志突然愣住,這個詞從陳瑞龍口中說出有萬分的違和。
「三太子在問啦。」
「三太子怎麼突然想知道這個?」
「有信徒在問啦,什麼基因的問題,不知道會不會遺傳……」
「你不是以前都跟他們說多做好事存福報就行了?」
「算了算了!你怎麼還沒去唸書?快點回房間!」
冠志不爽的走回房間,走到一半卻又被爸爸叫住。
「阿志,明天請假跟我去醫院一趟。」
「到底是怎麼樣啦!」冠志對他大吼:「你跟媽媽到底是怎麼了?」
「你以為我願意這麼倒霉喔?」陳瑞龍看著他,緩緩的說:「什麼失智症的啦。」
陳冠志僵在原地。
「有夠衰,你阿嬤也是差不多這個時間開始忘東忘西,有夠不方便……你那什麼臉,又不會死!你阿嬤從那之後還一直活到現在,又活十幾年了啦,怕什麼?我現在五十,再活個十幾年也夠本了!」
「所以…..你會忘記越來越多東西嗎?」
陳瑞龍突然覺得,眼前已經快一百八十公分的陳冠志此時突然變得好小好無助的樣子。
「媽的,你不要給我亂說!那些醫生說我會怎樣我就真的會怎樣喔?你爸爸我腦子現在只是偶爾秀逗,其他時候都很正常的!你叫你媽不要一直哭啦,看了都煩。」
「那我明天為什麼要跟你一起去?」
陳瑞龍無法開口。
所謂的失智症多發生於老年人口,然而在某些少數的病例上人們發現,失智症也會發生在低於六十五歲的人身上,他們將之定義為早發性失智症,在四十到六十五歲發生的機率約為五千分之一。其最大的特色為「體染色體顯性遺傳」,也就是說,一旦帶有這個治病基因,幾乎可以肯定一定會發病。
在醫院看報告時,醫生向陳瑞龍夫妻說了些讓他們已經一片空白的腦更加混亂的東西。
「這個致病機制就是大腦中一個製造一種叫APP蛋白的基因有問題,讓APP蛋白沒辦法被代謝,堆在腦裡讓神經細胞慢慢死亡。那因為我們懷疑陳先生有這方面的問題,再加上陳先生的媽媽也有,所以建議整個家族做基因檢測。」
「你是說我兒子有可能會得?」陳瑞龍瞪大眼睛,手上的筆握不太住。
「有一定的機率。麻煩你另外通知你的其他兄弟姐妹。」
來到醫院的那天,陳瑞龍反而擔起安慰親朋好友的重責大任。
許久不見,瑞昇似乎變胖了一點,升官變訓導主任了; 小文功課很好,將來和冠志一樣說不定都能念第一志願的大學。瑞慈保養得很好,拿到綠卡了,似乎結婚又離婚了,個性還是跟以前一樣; 她的女兒Kelly很會說英文,看起來有點怕生。
「大家笑一個啦!家族聚會欸!每個都死人臉!」陳瑞龍在醫院美食街看著大家。
「我不測了啦!我為什麼要測?我才十七歲欸!」陳冠志起身想走人,被媽媽按在位子上。
「我也不想測,提早知道自己可能會變媽那樣,讓自己不好受一輩子要做什麼?」瑞慈托著臉滑手機。
瑞龍和瑞昇去上廁所,瑞昇叫住他。
「哥,我看老家,就留著吧。」瑞昇開口。
「啊你跟瑞慈不是要錢?」
「我們來之前討論過了,怕有一天,我們都會忘記老家的樣子,還有彼此的樣子,還是留著吧。不要看瑞慈那樣,她跟我說她常夢到老家,後來的公寓反而一次都沒夢過。」瑞昇低著頭。
「哥,我常常在想啦,如果那個時候是我去學做法事,或是瑞慈去,今天我們家會變什麼樣子?」
「你想這做什麼?無聊!」
「我是要說,謝謝你。」
「欸!訓導主任!你哥哥我還沒死,講這什麼無聊的話!」
「也許你該去看看媽了,她最近狀況不太好,連我們是誰都忘了。」
瑞龍沒有回答,回到美食街去。
「我跟你們說啦!冠志你給我專心聽!」瑞龍回到座位向家人們說。
「我們媽媽,老是說她的命旺夫; 我呢?算命的說是關老爺的義子,小時候還聽得見祖先說話,大家都說是很有福氣的命,抓周的時候還抓到筊杯。我從小跟我媽媽一起賭啦,大家樂、六合彩到樂透什麼都玩,贏最大,贏到一棟房子; 輸最大,輸到一個失智症。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最差還不是現在這樣?」
瑞龍邊吃碗裡的湯麵一邊說:「就是拿命去賭嘛!怕什麼?我們陳家到今天還不是苦過來了?我們就繼續賭!好不好?說不定那什麼藥廠醫生今年賺很多,明年這個病就跟看感冒一樣,有什麼好緊張的?我下注兩千塊,你們大家都身體健康,算我比較衰啦!」
冠志拿到檢查報告的那天,是一個晴朗的下午。
醫院走道被夕陽染成金黃,看起來有點肥胖的父親慢慢走到他身邊。
「爸,我們都沒事。」冠志笑了。
瑞龍緊緊的抱住冠志:「我就說吧,神明和祖先都很疼我們,我是天公伯疼的命啦!」
冠志的情緒終於潰堤:「可是你…….」
他抱住兒子許久才開口:「你沒事比較重要啦!」
聽醫護人員說,最近陳李秋滿變得十分戲劇性,每開一次病房的門,都能看見不同的風景。
陳瑞龍深吸一口氣,與父親一起打開門。
「請喝茶。」一個年輕的新娘彎下身,將茶杯遞到年輕的先生面前。
她年輕的丈夫笑呵呵地接下。
然後他們在親友的起鬨聲中被送入洞房。
當他再度打開門時,看見了一群人,裡頭有個提著菜籃的女子大聲尖笑。
「我中了啦!我的兒子好厲害!我中大獎了!幫我數,這到底有幾個零?你們絕對想不到昨天我兒子到底發生什麼事…..」
而某次他開門時,看到了一個披頭散髮的女子在哭泣,她求神明幫幫忙,求祖先顯個靈,她的丈夫生了重病,小孩還小,她又不懂字沒辦法工作,求祂們透露幾張牌。她擲筊問:她的大兒子不讀書了,要被收去當乩童,以後人生會不會順利?要讓他去嗎?她擲出聖杯,但她反而不太高興,一直丟,一直丟,期待丟出笑杯。
又有某次,他開門時,好像看見父母與他們三兄妹即將搬離三合院時,幾個人在門口要拍合照。
不知多少次之後,某次他開門時,他終於遇見他母親。
「媽,我回來了。」
「阿龍!你回家囉!」陳李秋滿看見他呵呵笑著:「變這麼胖!」
「當乩童當得好啊!信徒很多,比以前家裡附近的土地公廟還多!」
「那麼厲害喔!」
「阿昇當到學校主任,阿慈有個女兒了,現在兩個人都過得好好的。爸身體還很健康,剛下樓去吃東西。」
「瑞龍,要認真打拼!注意身體!以後也要常回來喔!」媽媽笑著說。
「好啦!妳也要注意身體!」
某個假日,陳李秋滿狀況不錯,家人特地將她接出來。
他們來到老三合院前。
「瑞慈阿姨,妳再站過去一點,小文,妳頭髮撥一下!阿嬤看鏡頭這邊!阿嬤!阿嬤!」冠志拿著自拍神器,幫鏡頭中的家人調整位置。
「好,大家笑一個!」
陳李秋滿搞不太清楚大家在做什麼,不過此時的她回到要搬新家的那一天,他們還是幫三合院大門貼上新的春聯。
那副對聯好像是這樣寫的:
天增歲月人增壽,春滿乾坤福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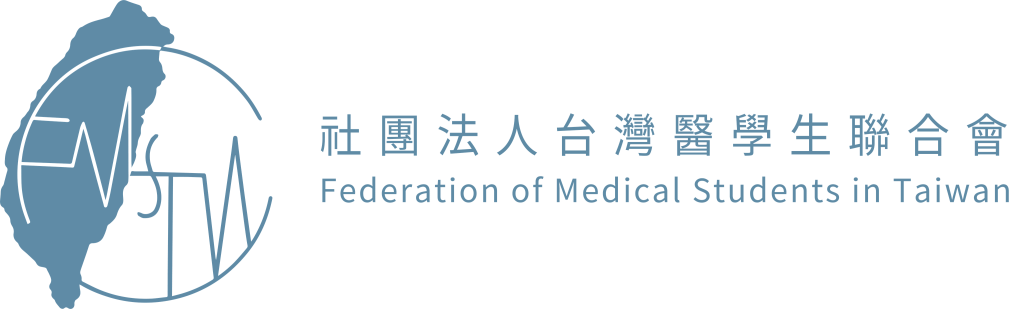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