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小說組佳作]國防醫學五-宋育凱《淨土》
我在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醒了過來,身旁堆滿的不知道是紙箱還是木箱。
待眼睛習慣黑暗之後,我環視了四周,發現自己在一個類似倉庫的地方。我被一片漆黑環繞,只有頭頂上方透出一點微弱的光線,整個空間充滿了陳舊的氣味。
我攀住身旁的箱子,慢慢的把自己往上撐,倉庫裡的箱子堆得比我想像的還密集,我很快就爬到了天花板高度。我找到透出光線的地方,用手掌先扶了扶,然後用力的撐開了那扇活板門,光線灑在我的身上。
出了活板門,我拍拍自己身上的灰塵,慶幸自己沒有被扎滿木屑。我在一座類似古寺的建築物的陽台上,走廊上也放了不少木箱。我試著移動自己爬出陽台,卻意外碰倒了旁邊一個小小的木箱,裏頭的東西翻了出來,我於是蹲下來查看。
「清玉白包──」箱內裝的是一個用白玉雕刻成的小籠包,和真的小籠包差不多大,還附著解說的字條。白玉略為透明,表現出了皮的吹彈可破,更顯得鮮嫩欲滴,可以看出此作絕非等閒玩物。
「白玉做的小籠包,襯著粗麻布,一起擺在酷似蒸籠的小木箱裡,可搭配的真巧妙。」我這麼想著,把它們安置好,放回身旁的木箱上。這是我不能夠輕佻把玩的寶物。
爬出陽台走進了樹林,樹枝間透出陽光,明亮而不刺眼。道別身後小小的古寺,我繼續向前走,眼前漸漸出現一道石階。
走上石階是一座火車月台,兩端空蕩蕩的不見欄杆、圍牆,只有遮陽的頂,看起來是個已經廢棄許久不再使用的車站了。既然沒什麼別的事,我索性坐下在石椅上等車,吹吹微風。
過了不久居然真的有列車進站了,是捷運的車廂,我找了空位隨意坐下。
列車開始開動,在低矮的山丘和谷間穿梭,窗外的景色盡是綠蔭而非想像中的水泥叢林,我跪在座位上,雙手扶著窗外像是孩子似的對著窗外張望,而大部分其他乘客都低著頭沉默地坐著。
令我感到好奇的是,從列車開始行駛以來,我便看到的許多特別的人,或是說,行為特別的人。
他們身著奇裝異服,有的單獨行動,有的三五成團,在鐵軌上等待著列車的到來,然後在緊要關頭跳開軌道躲避列車,他們穿梭在不同條軌道之間來回舞蹈著,無視這麼做的危險,甚至引以為樂。
「你也看見了吧?」正當我想開口詢問,旁邊一位穿西裝戴著高帽子的乘客開口了。我起先還沒意識到他是在對我說話,我正納悶為什麼火車的鐵軌會行駛著捷運的車廂。
「他們叫做軌舞士,這是青少年之間的次文化,」他把帽子摘下來說,「這是近十年來才發展出來,新的運動型態,通常每個團會有不同的規則和玩法,有些人把這當作是對文明開發的挑釁,有些人是為了向父母親耍叛逆,有些則只是想追求刺激。」
這解答了我部份的疑惑,但仍然解釋不了為什麼老舊的鐵軌會駛著先進的車輛。
我繼續看著窗外飛逝的景色,然後我看見了令我無法忘記的景象。
我們的車和另外一列車交錯,遠遠的就看見有一列人在前面等著,一待兩列車交錯便跳到兩列車之間,在兩條鐵軌之間狹窄的空間緩步行進,他們踏著整齊的步伐,沒有遲疑,沒有恐懼,一列六個人就這樣在夾縫中躍動著,輕盈的好像人世間的紛擾都隱形了。
簡直把這當作一種極限運動一般!
正當我看得出神,只見列子最後一個軌舞士一個不穩,輕輕搖晃了一下,然後便被另外一輛車狠狠地扯離了隊伍,往後方帶走了。
我坐回位子上,默念著他的安危。
「又是他們啊,這個月已經第五個實習生了。」旁邊看著報紙的乘客放下報紙說。
他剛剛根本沒有往窗外看。
「你剛剛看見的,是軌舞士的圈子裡面,技巧最高超的一團,」待高帽子的乘客微笑著靜靜聽他說話,其他乘客也抬起頭聽著,「他們不走花俏的舞步,他們不躲避列車,他們只在兩台交錯的列車之間行走。也因此,他們對每班火車什麼時候會在哪裡,比我們之間的任何人都還要清楚。」
「他們的組織架構很明確,越資深的走在越前面,帶頭的是團長,最後面的是菜鳥,這是他們前任團長退休之後,新招的第五個實習生了,看來少了有經驗的團長還是很困難啊。」他自顧自的說完就繼續看起報紙,其他人也低下頭回歸沉默。
車上的廣播響起,車掌告訴我們剛剛的事故已經有人去處理了,請我們不必擔心,受傷的年輕人並沒有生命危險,只是必須請我們換搭另一輛車。
我們換上了一輛更舊的車,座椅覆著破舊的皮革,橫桿上掛著圓形的拉環。
這輛車行駛的更慢了,我感覺我昏昏沉沉的睡去,只記得沿途經過了「龍巖」和「蔭之林」或是「林之蔭」之類的站名。
這片大地,究竟是被時間遺忘的多徹底啊?
等我再次回過神來天已經黑了,車靜靜的停在終點站,車廂內空無一人,我摸黑尋找出去的路。
眼睛還沒完全適應黑暗,我瞥見一旁的坐椅上躺著一個不小身影,我不由自主地叫了出來。
「欸欸啊,我不會吃人啦!叫成這樣也太失禮了。」黑影傳來低沉的男聲,他伸了伸懶腰,然後點了根菸。
坐著抽了一會菸後,好像再次意識到我的存在,他開口說:「剛才因為你怎麼樣也叫不起來,所以我乾脆關掉燈也先歇一會,沒想到你一醒來就大吼大叫。」我注意到他身材壯碩,髮鬚濃密,穿著無袖的牛仔背心。
「噢對了,你這樣應該沒有辦法出去吧,讓我幫你,」他打開門旁邊的操作箱,扳下幾個開關(車裡還是黑的),然後手動把電車的門拉開,「再見啦,叫不起床又大吼大叫先生。」他送我出門,然後又躺回椅子上去了。
我從洗手間出來,準備從旁邊的樓梯出站,卻被一個穿紅色洋裝的女孩擋住。
「不好意思,請問這個是你的鞋子嗎?」她指著自己穿在腳上的鞋。
「這不是你的鞋子嗎?」我問。
她搖搖頭。
我掃視了一遍她的整個人,臉不是很清楚(夜色的關係嗎?)但好像隱隱約約地微笑著,給人的感覺略顯端莊,身材,還不錯。
「咦,什麼,等等,你幾歲了?」我被弄糊塗了,有點胡言亂語。
「三十九。」她說。
我發誓她看起來絕對不到三十。
「等等,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一個三十好幾的女人,穿著不是自己的鞋子,三更半夜在沒有人的車站到處亂晃?」
她點點頭。
「你這個女人真是太有趣了,我一定要跟你好好聊一聊。」我說。
「不如,我們就一邊聊一邊前往妳的住處?」我搭上她的肩頭,一起走下樓梯。
第一次聽自己說出這樣搭訕的話感覺真奇怪,而沒想到我居然就這樣一路隨她走到了她的宅邸。
- (明明是在作夢,為什麼碰到十八禁場景一樣會跳過呢?)
隔天,她在宅邸的大門和我道別,她對我說,我想的話隨時都可以再來找她玩。
我慢慢地踮著腳步走下山坡,一邊觀察這個小鎮。
這是一個臨著海的小鎮,但四周被山環繞,給人一種像是九份的感覺,但整體來說更明亮而且溫暖一些,山坡迎著陣陣微風的擁抱。一旁林立的商家傳出食物的香氣,蒸籠透出一絲絲的蒸氣。我想想我沒吃早餐,嚥了嚥口水,肚子有些蠢蠢欲動,我一翻兩邊口袋──空的。
我啐念了幾聲,覺得不是滋味,只好四處遊蕩著,肚皮卻還是餓得打扁。
然後,在來往的人群之中,我看見了一個孩子。一個鄉下的孩子,看起來十歲出頭,穿著吊嘎和短褲,調皮的樣子。他看起來不像任何我認識的人,但給我一種親切的熟悉感,好像我自己的弟弟一樣。
覺得可以建立某種聯繫,我於是走向他試著攀談。我想暫且就稱他為阿弟吧。我同阿弟解釋我身上沒有錢,但肚子挺餓。他說他是被派出來小鎮採購東西的,如果採買完了錢有剩下,那麼可以讓我買點東西吃。
雖是這樣說,但阿弟卻先買了個包子給我。他說絕大多數時候採買東西錢都會有剩,剩下的就當作他的零用錢了。我吃了包子精神好得多了,覺得十分感謝他,便隨著阿弟一起在小鎮裡東奔西走,添足購物清單上的物品。
等到用品買足,阿弟停下腳步,問我接下來要去什麼地方,要不要跟他一起返往他來的地方。我說我沒有要去的方向,可以跟著他走沒有問題。他說我們不搭火車了,徒步走回去,我沒有意見。他找到了樓梯慢慢走下山,往谷底走去,看起來對這個路線很熟悉的樣子。
山谷不是很深,仍然是光線可以穿透的範圍。谷底不見大條的河流,只有涓涓細流,大部分的面積被草原給覆蓋,倚著山壁的地方有些樹林,但不是非常茂密。
阿弟沿途中很沉默,似乎是很專心的在走這條路。我們鑽過一棵倒下腐木的底下,翻過了一個大石頭,又跨過了一小段溪流。阿弟紮著穩當的步伐帶著我走,我抬頭看見山坡上列車沿著鐵軌緩緩地駛過。因著山勢崎嶇,鐵路蜿蜒其實繞了不少的路。
我想起了看起來老舊的鐵軌行駛著先進車輛的疑惑,仍然不得其解。
阿弟開口了,像是聽見了我的心聲,但卻又不是會令人感到害怕的那種。
「這片大地,原本是拿來耕種的。」
那個時候,雨季的雨量非常豐沛,山谷因為河流的灌溉,收成的穀物足夠供村裡的人自給自足,還可以稍微外銷,換取其他生活用品,所以才會建造這條鐵軌。
「但是後來,經過了好幾年的乾旱,山谷漸漸沒辦法種稻了,是還可以種得出些雜糧,但沒什麼利潤所以大家也不太種,商業才又慢慢發達了起來,後來為了商品的流通,原本的鐵軌又被用作新的規劃。」
這確實可以解釋古老的鐵路行駛著先進的車輛。
「這樣的確是給村子帶來了新的生機和活力,但也免不了對環境造成破壞,所以也有不少人反對這樣的開發。」
我想起了在鐵軌間躍動的那群軌舞士們。
走著走著,映入我們眼簾的居然是我醒過來的那個古寺。
這完全不合理啊,要坐火車到的距離,為什麼不知不覺,就能夠徒步走回來呢?
「所以,你是從這裡來的?」我問阿弟。
「嗯嗯。」他點點頭。
這讓我感到驚訝,但隱隱約約又覺得非得是這樣不可。
才一走近,就清楚的聽見寺裡傳來罵人的聲音。
阿弟留我在廳門口外,自己先帶著採買好的用品進去,我探了頭偷偷往裡面看,看見住持正對著一群小沙彌說教,內容聽不是很清楚,但似乎是弄丟了什麼很重要的東西。阿弟比他們年紀都稍長,進去替他們解圍,向我的方向指了指,示意有客人來,看起來很懂事的樣子。
住持朝我這裡看了過來,於是遣了小沙彌們先下去做打掃的工作,然後邀請我入內坐下。他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沒有回答。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穿的服裝,像是書生又像是遊子,也許是這樣他才這麼問我吧。
我詢問了阿弟為什麼不必剃髮。他長嘆了一口氣,說這些小沙彌其實都是孤兒,他是地方一個地主,把孤兒安置在寺廟裡才不至於流落街頭,受別人欺負或是被人口販子賣作奴僕。阿勇(原來阿弟的名字叫做阿勇)因為年紀比較大了,漸漸到了可以還俗的年紀,所以頭髮就不再特別理了,也因為即將離開寺廟自尋出路,所以派給他比較多會往外走的工作。
也許是意識到不該對初次見面的人講這些,地主停頓了一會兒。我覺得地主不像是嚴苛的人,便詢問了剛剛責罵小沙彌們的來由,是否是遇上了什麼困難。
地主皺了皺眉頭,又繼續說了下去。
地主說自己的農地因為乾旱慢慢沒有佃農願意耕種了,近日來的開銷都是依賴以前的積蓄,只是也慢慢耗盡了,又逢官員來收稅,沒有辦法只好變賣自己的寶物來支持寺廟的開銷。豈知小沙彌們在整理的時候,不知道把寶物收到哪裡去了,問遍所有人居然沒有人有印象,他才破口大罵,實在是有失身分,他感到十分不好意思。
「寶物啊,啊,該不會是那一個?」我喃喃念道。
阿勇方才一直靜靜的在旁邊聽者,此時卻像是想到了什麼一樣跳了起來,往旁邊走廊跑過去。我起身跟著他的腳步,地主也跟在後面。
打開一扇厚重的門,果然是那個積著灰塵的倉庫陽台,阿勇跑了進去左顧右盼,銳利的眼神像是在搜尋著什麼,又像是在嗅著什麼的氣味。
- (夢在此處左右醒了)
我走進走廊,示意要阿勇讓條路給我,然後走到旁邊拿起了那個小木箱。
「你說的寶物是指這個吧?」我打開內容給地主過目。
「啊!是了是了,就是這個,實在太感謝你了!」清玉白包在我們的眼前透亮著。
我們回到大廳,地主看起來很安心的樣子,他把小木箱放在大腿上,很珍視的捧著。我在他的對面坐下。
「真的是太感謝你的幫忙了,這樣一來我們寺裡的孩子就不必再為生活擔憂了!」地主十分激動地對我說。
我只是靜靜地。
「不過,你怎麼會知道失蹤的寶物放在什麼地方呢?」他又問。
「只是一個感覺而已。」我說。
我坐在古寺裡的椅子上,但我並不在這裡。我在我走過的每一腳步,我在我思索過的每一念頭,我觀想著整片大地,我思索其中的關聯性,我反反覆覆流轉其中的每一個。
「我想,住持你還是稍等我一下,」我說:「我在思考,或許有其他辦法可以不必動用這件寶物。這件寶物十足珍貴,必定有他的歷史意義,如果就這麼當作稅金充公了,很有可能不被妥善的保存。」
他低下了頭,似乎也捨不得這寶貝離開。
「施主有其他的辦法嗎?」他問。
「只是一個念頭,但或許可以實行。」我仍在思索。
「我沒有辦法保證,但請一定要相信我──不然,至少也要相信阿勇。」我說。
「那麼還請施主嘗試看看,只希望阿勇也有可以幫得上忙的地方。現在離繳稅的期限還有一陣子,施主有願完成的話可得加快腳步。」他說。
「那麼我和阿勇略作休息之後就出發。」我說。
我和阿勇步行前往小鎮,我打算再去拜訪那位孤單的貴婦。
到了小鎮,我沿著下來的山坡往上走,停在了宅邸的大門前,那是一扇雕著精緻花邊的黑色金屬大門,上方有些鏤空,看起來很沉重。
「沒有門鈴也沒有門環,要敲敲看大門嗎?」阿勇問。
「不需要。她在家應該也會四處走動,不會閒著。」我說。
我和阿勇靠著大門旁的石牆坐了下來,看著清澈的天空有些許雲朵飄過。
晴朗的大地啊!卻飽受著乾旱之苦。努力的人們啊!卻尋不著生存之路。
約莫半晌,背後的庭院緩緩地傳出腳步聲。
「所以我說我們不必敲門的,」我對阿勇說,但其實是刻意為了讓女主人聽見我們談話的聲音。
腳步聲漸漸靠近,然後在門上探出了一雙眼睛。
「啊呀,是你!」她的眼神閃閃發光。
她低下身拉開了大門,她身穿緞布滾邊的一席白色洋裝,身後是她整理整齊的花圃。
「你回來了!」她把雙手背在背後,微微彎著腰,瞇著雙眼給我燦爛的微笑,像是用她整顆心來給我深深的擁抱。
「又來添麻煩了!」我也輕輕彎個腰,對她微笑。
女主人給我們端來蛋糕,用鑲金邊的瓷盤盛著,她又在我的盤子旁邊放了一杯茶──是杯口有寬邊深綠色釉彩的歐風茶具──然後窩坐在沙發裡頭,捧著臉頰對我們微笑。
「不需要客氣喔!」她說。
我讓阿勇拿去我一半的蛋糕,然後啜了一小口茶。
「我再過一陣子,要旅行到很遠的地方去了。」我對女主人說:「或許沒有辦法保證,我什麼時候回得來。」
她皺了皺眉頭,但又瞇起眼睛笑著。
「好哇!」她領我走向她的窗台。
「這片花園原本是我先生在照料的,他很仔細的培育了一種四季都會開花的玫瑰,只要細心照顧都會開花。他總是說我對他來說就像是這些玫瑰一樣,我從前都不了解這段話的意義,覺得他只愛花,不夠愛我。」她望向窗外。
「你不覺得很美嗎?我先生生前,腦子裡面只想著怎麼讓這個世界散播更多的美麗呢!」
我點點頭。
「我先生過世以後,我有好長一段時間,幾乎放棄了自己,整天只是無所事事的遊盪著,任心中的徬徨在外表上呈現。直到你發現了這樣的我,仍然有美麗。」
我尷尬的又點了點頭。
「然後我開始動手,才發現總是看著先生整理花圃,自己早就也已經學會了。」
女主人說著說著有點出了神,輕輕地閉上了眼睛。
「這件洋裝是我自己做的,但是後來因為先生過世了一直都沒有穿上它,可我覺得自己值得這樣的美麗,即使帶著心中的悲傷。人也是這樣吧,只要好好照顧都能綻放美麗。」她仍閉著雙眼。
我望著角落裡生鏽的裁縫機,也幾近出了神。
「所以,旁邊那個孩子是你的──?」她把我拉回了現實。
「弟弟,」我不假思索。
「他現在待在一個地主支持的古寺裡,裡頭還收容了許多的孤兒。那些孩子們都很可愛而且懂事,我想妳見了一定也會喜歡他們,」
「不過近來他們的生活好像變得困難了起來。」我低下頭,只是輕描淡寫的帶過這件事。
「我了解了。」
女主人起身,走到了阿勇身邊,蹲下來低聲說了些話,只見阿勇不斷抬頭、低頭,在回答女主人問題和盤裡的蛋糕之間往返。
我決定走出門。我在階前坐下來,呆望著庭院背後的石牆。
院子裡的花叢隨著微風搖擺,綠茵叢中只有少許的粉紅色花苞,空氣中散著清爽的青草氣息,席捲但不艷麗。清風揚起地上的葉子,我感覺她也走出了門。
她走到我的身後,讓髮絲輕拂我的後頸和臉龐。
我只是靜靜地坐著。
「阿勇!該走了!」我喚著屋內的阿勇。
兩人一個深鞠躬向女主人道別。
搭上回程的列車,我們在龍巖站下了車。
遠遠的。遠遠的就看見有一群軌舞士在那裏等待列車的到來,他們原本是散著,或坐或站,或倚牆靠著,聊著天,但當我們走上鐵軌,漸漸走近,他們便各自站起身朝向我們,架著兩條臂膀──在一旁原本靜靜蹲著的那位,朝我們走了過來。
「有什麼事嗎?」對我們說話的這位壯碩青年帶著防衛性的姿態,口吻像是他必須為所有成員的行動負責,他的氣勢不容侵犯,也不侵犯人。
「你們是軌舞士──」我話說到一半就被打斷,因為後面有一個團員很不屑地大聲「哧」了一聲。
「──裡頭最頂尖的一群,對吧?」我繼續把話講完。
「確實,有些人這麼說,」他等著我繼續說下去。
「你們的表演讓我印象深刻,」
如我意料的一樣,後方響起刺耳的吵鬧聲。
「這才不是一場表演──」
「他不了解我們的信念──」
「團長,別被這種人的話語給動搖了──」
「想想我們付出多少努力才換得這樣的成果──」
「噓!不是敵人!」團長大聲喝斥,後面的團員靜下聲來。
「我知道我沒有辦法用任何方法取得你們對我的信任,我有個建議給你們,但我知道我得付出一些代價來換你們的一雙耳朵。」
「是,但你可知道該要怎麼做?」團長低聲笑。
「讓我當你們的實習生吧,」我說,「待會等交錯的火車來了,就讓我走在列子的最後面。」團長揚起一邊的眉頭。
「如果我一次就成功了,沒有被火車撞到,你們就聽我的建議;反之,如果我失敗了,你們就可以把我的建議當作耳邊風──」
阿勇皺起了眉頭。我知道他聽得出這不是一個有效的協議,不論我成功與否,對於結果並沒有差別,但阿勇很沉得住氣,沒有作聲。
「那我倒是很想看看。」團長放聲笑了起來,又說:「我可以同意,但我必須尊重每位團員的意見,離火車到來還有一段時間,讓我們開個會討論吧。」
阿勇無聊的踢著鐵軌上的石子。
團長一個人走了過來。
「我們的結果是同意讓你試試看。我個人是想聽聽你想說的話,但你知道就算你成功了,也不一定服得了所有團員對吧?」
我點點頭。
「雖然大家現在叫我團長,但其實我心裡還覺得自己是副團長的,因為一直還沒有再立副團長。我想,如果有一個挑戰成功的實習生,應該可以讓各位團員的角色更明確、更鞏固一些吧。」
我們又等了一陣子的火車,直到軌舞士們開始陸續站起身來,我便知道挑戰來臨了。
兩邊的呼嘯聲逼近,團員走向其中一台列車,我感覺到迎面而來的壓迫感,直直的走向列車不是一般人會有的經驗,我的視線變得異常的敏銳,從鐵軌傳來的震動好像火車頭上一粒跳動的沙子我都可以看得見。
「預備──」團長高聲的喊。
一瞬間,右側已經先被一列火車遮蔽,我趕忙同其他團員一起把手放下,貼齊身體,在火車之間就不允許再用手保持平衡了,我的身體被惡狠狠震了一下,我趕緊站穩身子,但現在不是佩服的時候了
身後另外一列車的聲音也從背後趕上,直到兩側都是高速移動的車廂,兩旁的氣流撕扯著我的鼓膜,我幾乎沒有辦法呼吸,我只能勉強抓住節奏踩著腳步,只是每踩出去的一步都如臨深淵,就好像只要往旁邊偏了一公分,兩旁的火車就會像磁鐵一樣把我吸過去……
一二三四,一二三──
居然!連數著自己的心跳聲都會數到漏拍!
──但前面的列子居然是那麼平穩的走著,不不不,現在不是感到佩服的時候,我壓低重心,假裝兩側的火車都不存在,我只是在兩條鐵軌中間筆直地往前走。我一邊跟上前方隊伍的腳步,一邊估算著兩台列車交會的時間該會有幾秒,雖說最多不該超過一分半鐘,但極度的專注耗費我大把的心神,全程感覺過了好久,好像每一扇車窗後面張望的眼睛,都清楚地映在我的腦海……
好久。好久。當右邊的車牆終於露出空間,我不支地朝右方的地面倒了下去──
阿勇發出急促的一陣驚叫聲──
我倒在地上,看見團長蹲在我的臉旁邊,團員和阿勇也圍過來看著我。
「我們可以過來一起笑你了。」團長得意的樣子,嘻皮笑臉著。
「我失敗了嗎?」我問。
「你失敗了,但也成功了。」他說,又向團員問:「都同意吧?」
「我不懂。」我問。
「以我們的規矩,是必須走完之後,能夠平穩地走下鐵軌才算是成功,我們才會認可你成為我們的一員──」
「那麼是──?」
「但你說的是沒被火車撞到對吧,那麼以你開出來條件你是成功了。」
「你們都同意吧?」團員們只是聳聳肩。
我起身拍拍身上的沙土,深深的吐了一口氣,緩緩的說出我預備好的話──
「離開吧。」
寫在團員們臉上的,盡是困惑。
「離開吧,離開這片大地,到其他的國度去吧!」
驚愕。
「在這裡,人們只把你們當作反動的勢力,沒有人會幫助你們。到了其他國度、城市,會有人注意到你們,傾聽你們的聲音──你們在這裡沒有力量,但當你們從異鄉歸來,可以滿載著力量。」
「可是我們只是一群年輕人,旅程之中該怎麼生存下去呢?」團長問。
「以你們的技術能夠有精湛的演出,這世界不會背棄你們的。」
「你們有理念,有訴求,那麼就離開吧,去尋找去爭取屬於你們的力量。若是擔心勢單力薄,在出發前號召其他的同伴吧,發揮你們的影響力。」
迎來五雙空洞的眼神,不知道是否有承接住我想傳達的信念。
停頓了好一會,團長伸出他的手,我們握手,然後道別了。
搭上列車,我遠遠的看見了五個團員搭成了一個圈,好像討論起什麼重要的事。
坐在車上,沉默了許久了阿勇開口問了我。
「你對說的要去很遠的地方旅行,是指哪裡呢?」
「某些你們去不了的地方,吧。」
我望著車窗外遙遠的山巒。
「喔?像是甚麼地方呢?」
「像是,類似醒過來之類的吧──」
說著說著我不由自主的笑了起來,這是什麼樣的傻話呢?我從未料到會從自已口中說出如此可笑的話。我直笑著,久久難以自己。
空蕩的列車隆隆的繼續行駛著。
我感覺時間輕快了許多,但阿勇好像陷入了沉思,對他來講時間應該漫長了起來。
回到了古寺,我向地主簡單地描述了情況,告訴他接下來會有鎮上一位富有的寡婦暫時支持寺廟的生計,可以想見寺裡一段時間會有新的氣象。我心中浮現了女主人和孩童們相處的歡欣場景。
「唯獨有清玉白包這個寶物需要妥善收存,可能會是未來古寺得以傳承的關鍵。」我慎重的對地主說。
一切安妥後,我佯裝必須要踏上旅程,向地主道別,並請阿勇來送我。我們走向月台,靜靜看著大地的景緻,等天色漸漸昏黃,我對阿勇說了一些話。
然後,我們跨回堆滿木箱的陽台,打開了地上的門,我緩緩的爬回倉庫裡頭,小心翼翼的,一如爬出來時那樣。阿勇在門口看著我,但他背著光,我只看見他頭的輪廓,看不見他的臉。
待我在倉庫底躺臥好,我請阿勇替我關上活板門,我看見頭頂上的光線漸漸縮成一條細線,消失成一片黑暗。
然後,我再次陷入沉沉的大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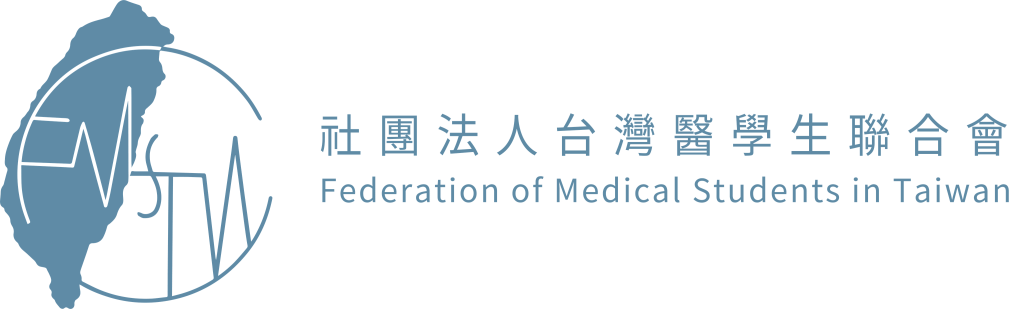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