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小說組佳作]陽明醫學六-林佳亨《巨人》
走過一扇又一扇厚重的鐵門,實習醫師宿舍走廊盡頭窗戶的馬賽克玻璃透不進多少陽光。最近幾周天空陰翳,據傳大陸霾害侵襲,室內杳無燈照,層層微光散射,塵粒飛揚,寒氣撲面。乾咳至今已有一月,止咳藥丸、甘草藥水甚至抗生素都服用過,究竟是流感或環境使然?讀現代文學所的友人建議我收集茂谷柑果皮,置於陽台曝曬三日,以熱開水兌飲,化痰之外尚收清嗓之效。
那橘皮水苦味濃重,說是良藥苦口,可我嗆咳後只覺胸膛如過往幾日他安放桌角的濡濕安全帽一般潮悶。那安全帽罩住他奔騰的情意穿過新海橋,「但願君心似我心」,到不了新莊廟口,那就看萬家燈火,非常浪漫。我的肺口灼燒,心房幽昧。此時此刻的他,想必同他妻女與學弟一家春遊,他將這活動喚作家聚。週一到週五他都在台北營區工作,周末才返回桃園家中,以此成就一個家。他貼心的女兒在小學作文裡頌讚父親對工作與家庭的付出,撰寫慶生日的美好回憶,歡唱《甜蜜的家庭》。這樣也好。醫學院裡的家聚通指相同座號的學長姐、學弟妹聚餐,學長姐分享求學與工作經驗,學弟妹暢談校園社團和課堂二三事。打十八歲北上求學以來,我依循如是的牽繫,學著自處異地。生活當真有這麼難?是否在這繁花盛開的森林中,我攪和太過?從來沒看過日出,再大的考試都儘可能讓自己早睡;若心情鬱悶,只管披著遲暮再多跑一公里。體力方面我不成問題,過去還住居石牌時,傍晚我總騎自行車到北體,隨那些收操的田徑隊員在操場以五分速奔馳,場邊常有年輕父母陪幼童丟飛盤或放風箏,北體的詩欣館旁有較強的高樓風,他們就抓準時機,在那一帶助跑、拋丟。我長期以來淺眠多夢,好幾次我在夢中跑著跑著就飛起來,飛得比林立信義區的商業大樓都高,然而我多想迫降,因為夢中的天空沒有風箏更沒有飛盤,呼嘎作響的疾風只令我想到年幼時與雙親在九份石牆腸徑間走散。
十八歲離鄉後,幾次行經水金九,我注意到遊覽車路線常順經青雲殿。從柏油坡路望去,可看見一片湛藍的灣海。峽澳圈圍古參眾生的有限、悲悽與那沛然莫之能禦的命運。幾年前在楓紅時季,我與隨幾位籃球隊隊友觀光,他們偕萍水相逢的星國遊客在老街尾排隊買芋圓,我沒胃口,便獨自穿越人潮,在死胡同前轉了個彎,踅進磚瓦錯雜的巷弄。有的房舍被漆塗各式符碼,有故事性的、有紀念價值的、有國際感的,九份究竟是怎樣的地方?五、六十年前傳承墾祚精神的那竿人都到哪了?我側身,在一間皮飾店旁暫倚,我對著夾腳拖鞋露出的腳趾甲溝發楞,眼角餘光納進一名年輕男子,他時而端坐在斑駁的木製國民小學四腳椅,時而伸手探進花襯衫裡搔抓,接著將身體重心移轉至骨盆,開腿蹲坐於地,宛若金蟾。我注意到他腳蹬一雙亮面漆皮男鞋,腳踝露出一截尼龍材質的深藍色襪子,那打扮不算過時,然更似日本撤退後那幾年以菸、以書餵養自己的憂愁青年,他們可能賴柔媚女人豢養,女人恐怕為他們的藝術家氣質傾倒,女人們有時探詢、或只是仰貼,如蜷伏的孟加拉母虎,浴饗時代鋒利,私下竟是寧不賴雄性動物,也願肩扛重責,見證天倫與時代交相覆滅。在我身旁的花襯衫男子其實是那年代的闇影吧,他怎麼就任憑肉身似卡榫般膠著在不合適的地點?豔陽不屬於九份,我印象中的九份總是下雨的,那日頭火球已不是殖民的借代,人們如今只透過私小說或詩喧嘩;面對過於批判的,人們的感受儘管無窮盡,卻是第二輪的,不談政策,只沉靜地透過鏡頭凝視街頭的槍與玫瑰。
「咖啡太澀,暫停一下,我去櫃檯加點起司蛋糕。」我們在短篇小說讀書會初遇,當天讀的作品是村上春樹的《遇見100%的女孩》,題材質軟而能引起九零年代前愛書人討論或援引,「你要不要吃?也有紐約五街。」
「花生厚片好了。」我看向咖啡店窗外,馬路上流連的日本僑人與金髮跑者,操簡單的外語,不疾不徐,逛著、看著,實踐他們心嚮往的有機生活。儘管天母已不若過往那般熱鬧,許多店遷移到內湖,可只要住民留居,便能在「茉莉漢堡」那樣的店,學ICRT播音員用鼻腔共鳴點餐,聽在地友人暢聊廚師在洋人家庭幫傭的故事。
「我老婆跟小孩很喜歡去一家咖啡店,裝潢可人,你一定會喜歡。店名是法語,裝潢概念來自一個日本設計師的系列作品。有的連鎖書店或日式百貨專櫃會賣熊貓或兔子的馬克杯對吧?我女兒很喜歡。要強調,我對那個沒有興趣,杯子就是杯子、稿紙就是稿紙,不是棋盤,更不是綠豆糕……」他停頓半秒,我無聲地還以他瞇眼張嘴笑的滑稽表情,「中年人的笑話啦!讀過那篇文章吧?我們年代應該沒差那麼多。我要說的是,我喜歡簡約的東西,生活越簡單越好。曾經帶你去過我台北的房子,不是多好的地段,屋齡也超過十五年,可是來訪的人都會稱讚那充滿南洋風情的地毯和起居室的海灣海報,十足讓人放鬆。那些都是拍賣網站上找到的瑕疵品,地毯有燒灼痕跡、門簾接縫脫線,那都無傷大雅!房子對我這樣工作與身分的人就像旅館一樣。讀書會那天我跟大家分享我的工作內容:有無良學弟、無理老闆。我的態度是,你可以選擇早晨在便利商店買一杯咖啡,讓店員送你美好的招呼;或者你可以開車,去倉儲量販店買濾掛咖啡,沖泡專屬自身的一天——生活絕非僵化而一成不變。」他是如此迷人,我只管專心聆聽他話中描繪的生活細瑣,從微波爐到冰箱,從洗衣機到浴室壁磚,都是他巧思點綴的花招世界。
他在女兒強褓時期會用被褥上的圖樣講述無價的想像故事。許多歐洲童話多取材地區風俗或傳說,內容代代流傳,經人蒐羅謄寫,最後於當代翻譯,裏頭的普世價值與道德精神令故事裡的角色失去辯白的機會。與其在文字中採擷敦良的德行,不如認識人的矛盾,他認為<圖書館奇譚>有助於此。在我看來,那樣超現實的故事如是解讀有些俗氣,然而最重要的是他對這樣的故事有感覺。
「你看《遇見100%的女孩》裡面還有一段文字提到煮義大利麵,那是我的憧憬。我在家不太下廚,出於無奈,多半外食,我太太在教科書出版社上班,有時候要處理教師手冊排版等等,庶務繁雜。兩份薪水,教育基金和房貸——恭喜你,未來二十年依然屹立的生存主題。」他啜吸一口已有些涼掉的咖啡,順道用指甲摳了摳鼻尖粉刺,「我太太和我母親處得不好,我媽有多發性硬化症,這幾年才發病。有時候一住院就是個把月,不可能一直請看護,所以我太太為了照顧她,時常換工作。我可以理解她有理由不討好我母親,但我不能接受她不照顧她,這我無法讓步。我可以在外頭、在台北,拼命工作,早餐吃一片吐司省錢,但我希望母親和我們能像大多數家庭那樣圓滿地住一起。」
那他的父親呢?從未聽他提起父親。那回他邀請我到他台北的家,樸拙的油漆掩蓋不了壁癌的痕跡。他舉起健壯的雙臂,背對我,褪去平整潔白的筆挺襯衫,腰際的皺褶倏地被他耷拉得令整件襯衫都變形,我好像看見一張人臉,那是一張扭曲、醜陋的男人臉孔,酸汗經年刻蝕著魚尾紋,法令紋牽動咬牙切齒的惡質嘴角。《深夜食堂》曾有一則短篇故事描述中年男子掩鏡自照,驚覺原來自己與記憶中的父親極為相似。「老了啦。」食堂老闆抽著菸如是說,我敢說那菸味不若萬寶龍那般溫雅,可店裡氣氛應比床尾男人的事後菸更妥貼。我記憶中的父親總身穿齊整的西裝出入家門,我從未見過他在同事或下屬面前是怎樣威風雄辯,那深藍的布紗網住錢鈔、窯篩幸福,可是愛呢?父親的愛都莞爾惜嘆了啊。我知道他沒有兒子,他儘管愛女兒,我仍深信他想要一個兒子、乾兒子、乾弟弟……
我可以化身。後來讀書會有一回我們閱讀王定國的<那麼熱,那麼冷>,他在我的筆記紙邊角書寫幾行字,直言他讀不到一半便棄卷,他不覺得那是人生的真相,可是作者說教意味引發他表層的閹割恐懼,他覺得不能以介乎有情無情的曖昧路數鋪張中年男子的故事,那種機關讓他焦慮,他在蔡瑟芬的官能式感知中探發無處可去的困窘,那囗那宀開闔關閁,手指血刃,飯菜因此鹹;時花謝落,蜂蟲無以養。我說可是這個解法會不會令故事比袒胸裸背的《台北爸爸,紐約媽媽》還要和平、還要光彩。他說他沒看過,但他聽過書名。他在紙上續寫,那花在遙控那些裸女,花甚至可能現身,男人就是招惹不起,也得硬著頭皮上場,那是命,不能解作噩運。這是我忖度他話中話的開始。罹病的母親、缺席的父親,龐大的肌肉,有沒有可能都是創作,創作若予人擬仿之感,那何妨說是孑然的贋作。我沒見過軍營中的健身器材,會像縣立體育館那樣,滿斥體臭、低吟與銹鋼嗎?我的問題太多。他索性揮舞彈力棒,耍弄著交到我手上,要我順臂膀的關節與肌理,令彈力棒像身體器官般向軸彎曲。
痛。
他喚我親愛的,逕自接過彈力棒,然後抬腿,黑色西裝褲瀕臨炸裂,有一股未知的力量,穿過織理——啊!我的父親!我的好爸爸!你在這裡嗎?我能不能摸、如果我摸了——我的喉頭緊縮,口水盈滿會咽……彈力棒晃拗,那角度讓我駭怕,我聽見他菱形肌隔著大圓肌和小圓肌慘叫,那紋理和我細長的手指可能吻合,我能用我的手撫觸、遏止那一切違背重力的力量嗎?他的肩會疼,可是沒有藥讓撕裂的腱肉締結如初,亦無其他杳無險害的方子。曾有一整年他以為,若只是要坐看傾頹衰萎的臭皮囊,會不會在擎天崗已很有感?他卻偏要蹲坐在北投溫泉池裡,生肉鮮肉咕咾肉,自許什也不令他分心,芳情如他的妻,還要靠他開車四駛台灣東南西北郊遊,背著樓房貸款出走幾天,電話轉接,賴會未讀未回。好在我有時忙碌,期刊閱讀、病例報告、課本章節選摘,如早餐的潛艇堡,五彩繽紛,雙手一捧,免不了遍地散落。
「我覺得這樣很好,我從你那邊得到不同工作場域的經驗,然後回饋我自身的生活體驗——對了,你剛剛談到九份,你看見一個男人……」
是的,我們再回到這個主題——事已至此對他的重要性終於不明——我當時產生一些思想,可能盡是不合時宜的微觀和註腳,卻曾有通靈的朋友說,觀察力與洞察力過於敏銳之人,好幾世前可能在天界照看仙桃靈果一類,那工作需謹防偷取,耗損精神、眼力,是以現世才偶有靈感或靈視。可我高中國文老師提醒,讀書人正氣較一般人強些,多數房東其實私下租賃凶宅與學生,意在以正氣鎮壓或淨化。千頭萬緒盈滿漿腦……我如觸電般拔腿狂奔,也不明方位,直衝向青雲殿,我知道裡面供奉靈寶天尊和製藥仙童。原先乃為了傾訴什麼,到他們跟前我竟緘默。悻然離去時,我從龍柱的孔洞中望見海。
「那海有多深?」他自認擅分析、精謀略,認定掌握自身仕途晉陞的箇中秘訣,那使他目光如炬,有時也目光如豆,我認定那是因為他不懂山,也不知道海。我曾推薦讀書會成員《複眼人》這本書,我想讓他看阿特烈心眼中那超越語言的海,還要讓他直視達赫記憶中島上那變亦未變的山。
『海不健康了,山也不會健康的。』我將這句話寫在我們讀書會當時共食的窯烤披薩紙盒上,他聆聽過另一個讀書會夥伴對垃圾渦流的解構之後,皺了皺眉頭,才將目光聚焦在我的筆跡,隨之寫下:「父母是孩子們的鬼。」這段互動令我背脊發涼。他可能想維護家庭的完整,他沒有機會再期待多元成家;他可能只當我是不同領域的年輕朋友,他多的是機會認識精實而有活力的阿兵哥。我感到無比噁心。我悄悄羅列幾年來遇過的已婚男子,他們懷抱各式理由與故事靠近,隨之在衣領左右、哼唱之間、駐足之際掉落妥貼收藏的折翼青春鳥,然後斜睨與他併肩的年輕人,孤芳自賞地假定那清澄的雙瞳與彈簧般的小腿必然也將折損得辨識不能。他們期許自己能見證那孤絕的時刻,甚至有時汲於確認,僅僅依形象、數字、談吐就造了個畫框,從旁凝視,看那光滑的手背和腳心隨時代遊行。
他是陸軍,站哨或操練時不曾想到洋流和潮汐。海不是什麼恆常不變的東西,更不是溫柔得只剩母性的自然。醉酒漁夫會被浪舌自鯤鯓劫至東港。虱目魚苗成長的等比周期愈發壓縮。我們不是處於對等或依存的立場與海對話的,我們甚至聽不懂海風。行軍如他,從醫如我,不管如何轉身,都被海包圍了。之所立足,其實都不屬於我們——不安和困惑都從海得到解答與救贖,就算陽世有緣末了,就是化解的契機隨他分心、迴轉便令我落空,海竟是恆常地包藏我們。
我們都不篤信基督宗教,可我們對遠藤周作的《深河》深有共感。他在醒酒囈語中曾提及印度之旅的可能性,他可惜曾有那麼一張約定好的賞櫻機票因對方不接受他已婚的身分而作廢。他說那都過去了,我們就去泰姬瑪哈,別帶太多東西。兩人曬得一身黑,最好臉還髒得難以分辨,在南國的燠熱與潮悶中詩化碩果的甘美瓊汁。我告訴他我們去恆河洗澡,那顏色可能像極他喜愛的咖哩烏龍麵湯,清濁辛甘,指節就是竹箸,體垢何妨搓成條,黏纏糾結的髮絲可以是切不齊的蔥末,若散置的岸邊行李被偷,儘管任其浮漂如魚板吧。河要索求什麼,我們就心中捧花,想像花粉從指腹灑落趾尖,天人五衰,多麼幻滅,坐觀美停駐,待預言乍現。
『沒事了/封印已經解開/從此可以相愛了。』他私下其實讀詩的,只是他常搬弄插科打諢的雙關語,唯獨氣溫尚屬宜人的夜半,黃湯下肚,他才會躺臥在象牙色的沙發上,緊抓原先他要送給女兒的達菲熊玩偶,低喃幾句他或也忘記出處的詩句。我有時候憑印象,賴隻字片語在網路上搜尋,然而往往未找著全詩,他便低頭緊緊環抱。只有在這麼無防備的狀態下,我才得以注視他頂上日逐稀疏的髮絲。我身長近一米八,他身材並未高過於我,卻有一身勁力而能在宜蘭火車站旁的幾米公園臉不紅氣不喘地引體向上甚至轉體倒立,我曾上前嘗試,卻怎麼也翻轉不過,還踢倒他手中拿著的微糖綠茶。我倆首先發愣、大笑,接著他要我當心落地時別讓飲料弄髒白色帆布鞋。他瞥見遠處有兩佝僂女清潔工正分類保特瓶、鋁箔包與瓶蓋,我便從背包裡拿出一大包衛生紙蹲踞擦拭飲料的漬跡,他直對我說,這將是來日會心一笑的回憶……
藥商送的黑色馬克杯底總算再沒有任何一滴橘皮水,可我總覺仍有口膿痰深卡在肺內或細支氣管,於是便從茶水間再走回房內,向忙著為生活用品拍賣網站做動態廣告剪輯、配音的實習醫師室友要了包玫瑰花茶。
「這也是公司產品。你手中那種大小的杯子泡起來可能太濃,我給你我的保溫瓶,泡完後分我一點。」室友對接案內容並不特別有興趣,那有點侷限他無邊際的創意和拼貼能力,事實上於他來說,只要擬定工作流程與每日進度,甚至在我值班時間換鼻胃管的空檔,他在衣櫃便能完成三十秒短片所需的各種效果音和人聲測試。有時候他用電腦程式潤修錄音檔的音調和音質,就能展演完全不同的個性和人格。或許也能為我複製他說話的嗓音,甚至摹擬得好似他的人中與山根就在我耳根邊振動。
『開水很燙,請小心使用。』玫瑰花茶茶包在杯底鼓脹,隨水汽懸浮而上,乾燥花都隨溫熱散開,不復為綻放盛開時的模樣。我將茶水間的落地窗打開,遠眺高架橋彼端的車流,我想起那天我在他的邀約下,從劍潭搭上往桃園的客運,一路上我聽清水翔太的節奏藍調歌曲,真有那麼一點浪跡天涯海角的感覺。按他的指示,我在中正藝文特區下車,隨即震懾於眼前林立的大廈,晶亮的玻璃轉映往來汽車、雲朵的側影,究竟哪一棟可供常民住居?名稱可互相代換的物件頑固地展延在房產高專店前,黑髮女性身著襯衫仔裙,臉上大器卻不妖嬈的妝吸引仍不慣習黃色領帶的鄰店新手業務。我在路口那端看著兩人不約而同拿出最新型的高科技手機對看而後低頭搜尋。我與他的關係是否就是如此?交相搜尋,互放光亮,註定錯身。姊幾天前才提點我,何必選擇此人走一段誓不幸福的路途……可我願奉上我能給的籌碼,與這表面陽剛的男人賭一場陰柔的情話,能蹉跎到哪就到哪。
「這裡是我家附近,不要擔心,我家人都忙。熟識的學弟來,我也會這樣帶一輪。你看右手邊那家飲料店,非常多人排隊,有名的是紅茶拿鐵粉圓,不過你懶得咬粉圓,所以我再找找……炸豬排!這家連鎖豬排店很多台北人覺得好吃,但我就不再帶你吃桃園分店的東西。這種店是這樣的,有一套經營模式,複製改良再複製,很容易上手,我也在考慮幾年後退伍來開餐廳,我很有這方面的統籌能力,」他將方向盤往左轉二百七十度,「當時我就請我學弟投資我那新房子的裝潢,每個人不必負擔太多:五萬元!一廳三房一衛浴,我只會用到一間臥室,其餘兩間他們可以隨意帶人回來住,只要先跟我敲定時間,在不打擾彼此生活作息的前提下,下班後大家可以有個地盤吃喝玩樂,我覺得非常划算。可惜那些學弟口頭上說好,到了要拿錢的時候卻臨陣退縮。」我欲點頭稱是,卻不住乾咳幾聲。
「台北空氣很不好,我們營裡也很多人咳嗽。我現在很少開車就是為了環保。早起二十分鐘搭捷運上班不是太難的事,雖然要犧牲早上開車聽廣播的時間,電台有時會重播我喜歡的歌:李榮浩的<喜劇之王>。『站在我旁邊/你不算可憐/這也是種貢獻』,十足逼人,男人的歌!弟弟,你乍看成熟,其實很多生活經驗還要慢慢體會,才懂得那歌詞的妙境。」黃白色路燈透過車窗折射,照亮我胸膛前的安全帶和喉頭隆起。我有預感。歷經幾次與人相逢或親友痼疾亡故,關鍵時刻的預感都變得敏銳。那晚他決定在一家白飯無限量供應的火鍋店用餐,價格親民,他堅持買單。我的泡菜鍋摻料過鹹。那滋味讓我想起好久好久以前,在恆春古城,有一道狹窄的巷,巷的彼端有一道鐵拱門,門的彼端究竟有什麼我早已忘了,然而我明確記得那圓拱之高帶來的壓迫感使我同《傑克與魔豆》故事裡高聳入雲的豌豆樹連結。那拱門之後可能就是卡夫卡的城堡,若真如此,那在我有限的表層記憶中,我曾在那城下吃過一場壽宴,那年外公才七十歲,幾支親屬盡皆到齊,少不了鮑魚蟹膏魚翅羹,那羹黑醋加添過剩,就是多配幾口油飯或蒸石斑亦安撫不了舌尖麻利,我多想配白飯吃,可筵席少有人備辦白飯上桌。拗不過我,母親拿著紅色塑膠碗,挨家挨戶同鄰舍要來熱飯,我早食不知味,任性後帶來的訕笑令我困窘,我原本瘦小的肢體好似縮得更小,多麼想將身體藏進碗底,用白飯掩著,或鑽過拱門,看看那端住著誰,他們都吃什麼、靠什麼生活?我轉頭望向父親在鄰桌敬酒的背影,目光沿父親身著白襯衫的寬闊肩胛,骨碌碌地描畫父親的身體,父親好像變得比記憶中其他模樣還要巨大,對了,父親可能就是故事裡的巨人。
而他剛巧也是巨人的年紀。
「問你一個問題,」眼前的巨人放下碗筷,面色難掩沉重卻又溫柔地注視我,那是我不熟悉的態度。我調整自己的坐姿,扶正心中的歪斜,側耳傾聽,「我媽最近又住院,發燒、泌尿道感染,距離上次住院相隔不到半年。」
他的表情沒有變化,身體沒有形變,我懷疑這唐突的話題背後有其他計算。
「像這樣的狀況,你覺得她還有多少時間?」
『天上的主啊,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王國降臨。請饒恕我們的許多罪過。請賜福我們微小的每一步。』
『你是誰?為何人們得在你面前袒露胸懷,揭開自尊,好讓你看到他們赤裸的價值和無愧的自尊?』
菲律賓的季節可粗分為乾季和雨季。有醫療團在乾熱的十月造訪馬尼拉市郊的街巷,覺吃食油膩、衛生堪慮,代謝症候群和未矯正的先天畸形,相機捕捉著、幼兒追逐著。自磚瓦鐵皮橫陳間打水,斜陽從細隙灑落點點,石階騰躍過去還有一條巷,巷的盡頭又見上行的坡坂。手錶儘管沉睡而無時差,貓犬亦罔顧日晷,唯獨圈養的仔豬嘰鳴,屋舍的陰影有笫席和腳皮,無華亦無威嚴,好似幾年來動也不動隨氣蒸暑溽為晾掛的衣服上漿。診斷、分期和預後都不要了,藥物和縫線的意義也拋卻掉。在九份山海坐擁的靜謐,又回到心上。我們要活著,就得道謝、道歉、道愛、道別。
「你真的很有趣,」他穿上前幾周新買的羽絨背心,「我不太跟別人談自己家裡發生的事,但你的觀點和思考脈絡非常跳躍,這都很好,我從來不曾想過……是不一樣的世界。你要保持你現在這個樣子,做你自己,我希望你開心。」我需要傑克的勇氣來面對眼前的巨人。
「帶你逛逛我們這一區最有名的烘焙坊,幾年前有一美食節目來做專訪,現在供不應求、訂單不斷,特定種類的蛋糕不提早預約還真買不到。我們家只要有重要節日,比如母親節或小朋友生日,都會來這裡買,儘管蛋糕只是看起來一點也不費工的奶油海綿蛋糕,樸實無華,不過好東西都是這樣。蛋糕在低溫下的保存期限實際上可以超過兩周,所以選擇這種交易量大的店,才能確保商品的新鮮度。」他從架上拿了一條牛奶吐司結帳,然後從櫃檯抽一張廣告訂單遞給我。我單手接過,百無聊賴地收進背包夾層。
「最近醫院在擴建,粉塵很多,把落地窗關上。」室友霎然從茶水間旁的冰箱探頭,打斷我飄渺的思緒,「我昨天和護理站團購銅鑼燒冰淇淋,要一起吃嗎?」
「不過我今天值班,等會兒主治醫師和總醫師要查房。」
「那就等你跟完查房回來再一起吃。」
「配玫瑰花茶嗎?」
「等你回來都冷掉了吧,我還有阿里山茶葉,回頭再沖一泡來喝。」
「是好茶哪。」
「致純淨心靈的永恆陽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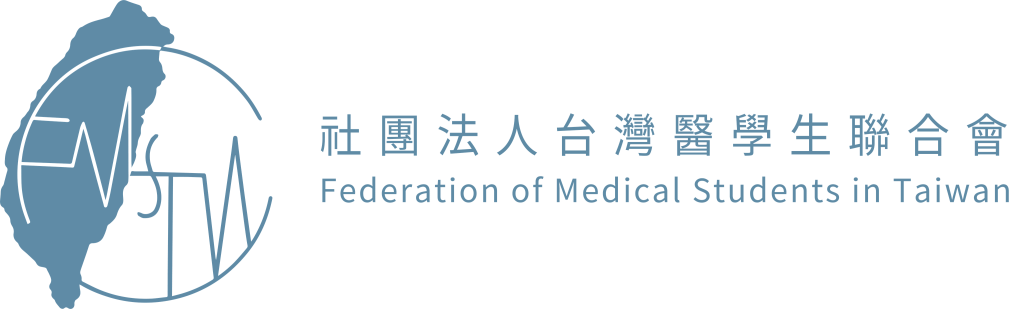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