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小說組首獎]陽明醫學五-王昱婷《野狗在我們的村莊》
今年北部的春天,有很長一段時間,總下著黏黏的雨。人要出門,穿雨衣、打了傘,進到屋裡,還是一股酸酸鹹鹹的滋味停在髮間,叫人沒一刻能神清氣爽。均至窩在租借的小套房裡,索性哪也不去,只看著窗戶上自己的倒影,傻愣傻愣的。聽外面不時傳來野狗成群的吠喊,不禁擔心著今晚的窗子,會不會就這樣灰暗一整個晚上。
母親是捎來電話了,但均至等的不是她。首先問候天氣、接著關心課業、再來便交代女孩子在外要學會自保和自我照顧等等的話題。總是這樣的。均至嗯嗯嗯的回答,想著在那個東部的小村落,首都人想像的寶島後花園,大概還一如既往的流淌著一股貧窮且晦暗的綠吧。趁著室友品妍不在,她把電話轉成擴音,讓母親的聲音在房間裡傳播。空出來的手可以做一些重複無聊的消遣,比方說,把保護易碎物的泡泡紙捏爆,來增添這場冗長對話的趣味。她想母親是聽不見的,因為面對她的沉默,母親也只是心平氣和地說,那裡的家,當然也下雨了。雨點像拳頭大,村長還廣播全村的男人去搬運沙包袋呢。
「原來都是一樣的。」均至捏爆最後一個空泡,從電話那頭聽到勇凱哥的狗吠叫的聲音。電話的收音系統不夠好,不然這時候應該已經聽見勇凱哥一腳往小黑的肚子踹去,大罵:「見鬼啦!叫啥?」阿莉姊死後,勇凱哥怕她的鬼魂真的回來找他,便對小黑沒頭沒腦的叫特別憎恨。
「怎麼心不在焉的,該不會不愛跟媽講話了吧?」母親的聲音把均至拉回現實,她越是疑神疑鬼的這樣說,就表示要結束通話了。均至吐了口氣,趁猶豫的時候,順手把套房的窗子打開,用拳頭試探著。冰冰涼涼的雨點擊在手背。
「想甚麼呢,我當然愛妳。」
「我也愛妳,早點睡,別忘了要寫信。」
但均至把筆擱在桌上,沒有睏意,也想不到任何可以下筆的句子。村莊在下雨,城市也在下雨,不管待在哪裡,應該都有相似的冷清。她聞到一股濃濃的香水味,從品妍的桌上傳來,混著雨水,好個煙花酒樓的氣味。看著窗上呆滯的臉孔。頭髮,還是高中解禁的長度,額上則剛冒出一顆白頭痘痘。記得剛搬進這間套房的時候,品妍看著她空空的化妝櫃架,很是吃驚。「不保養嗎?」均至搖頭。「穿這樣就出門?」均至猶豫了,像個算錯數學的孩子,驗算著答案。「妳噢!要不要來跟我學學?」品妍把眼睛笑彎成一條線,又長又密的睫毛像脹開的河豚把刺往兩旁展。她每個禮拜更新衣櫥,網購新衣,試穿後不喜歡的衣服再捐出去,覺得適合均至的就送她,「喏,妳都交男朋友了,有時候穿件裙子啊甚麼的,他會很高興的。」均至拗不過品妍的熱心,乾脆把衣櫃開著,讓她想塞甚麼就塞甚麼。等等常德要來,均至隨手拎了件衣服,蕾絲滾邊低胸短洋裝,大紅的,吊在那裏好幾週也沒穿過,光看著就寂寞。但她寧可把胸前的扣子解開一些,也不要穿那件洋裝。洋裝跟阿莉姊的風格太像。大家雖誇她美,經濟獨立,離了婚自己帶小孩,但她在山下的大馬路邊賣檳榔,母親每次看見她,就慌忙揮手,像要趕走白淨流理台上停留的蒼蠅。
而且,母親也會跟爸爸吵阿莉的事情。小時候,爸爸常要均至作證,說他去找她都是趁著均至去市區補英文的時候,順道經過的。「妳說,我難道有亂來?」均至據實以告:「爸爸沒有亂來,爸爸只是提醒阿莉姊要去做子宮抹片。」看到母親臉孔還飄盪著一股猶疑,只好再補句話:「亂來的是勇凱哥啦。爸爸根本沒有機會。勇凱哥每天都去找她,給她一百就多摸一次。一摸就摸很久。」沒想到母親這個也介意:「看這個!學這個!你這當到醫生、做人家老爸的良心過得去?不怕小孩長大有樣學樣?」均至還沒機會反駁,兩個大人吵得小平房都要炸開了。她想說,她根本不會長成阿莉姊的樣子。她不相信自己會有大胸部大屁股,那時候她年紀還小,讀了很多童話故事。她相信她會找個好老公,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一陣白光刺痛眼睛,均至的臉在窗上熄滅了。往外看,隱隱約約可以見到常德正跨坐在腳踏車上對著她招手。腳踏車停在套房外正對面的小坡上。一長一短的燈閃爍著。車前燈一開,窗一亮,不需要手機,均至就知道要出門約會。她趕緊把衣服復位,匆匆拿了一把傘,常德已經在門口把傘撐好。
「妳的家庭作業,寫好沒?」常德一見均至就打趣的捏捏她的臉。「別說了,我再想不出來,就打算把生活與藝術的學期報告寄回家。」常德牽著她往外走,並沒有像平常,會從包裡拿一件雨衣讓均至穿上。走了一會,均至才從剛剛的恍惚中回神,問:「不騎車?」「不騎,我們走去一個秘密基地。」雨很大,均至忘了穿防水的鞋子,走幾步路,踩進一個水窪,球鞋便發出噗嘰噗嘰的水聲。她想起國中的時候,有個晚上村子的雨也跟今天同樣失控。那是國一期中考後一周,剛發下考卷,她的生物考得失常離譜,放學後便在連綿的鳳梨田之間走著。夕陽絕望的墜下山了,天空滿布火紅的彩霞,聽氣象預報說是颱風天,路上的行人都躲回家。十三歲的均至心情不好,只想晃到全村唯一五彩繽紛的地方,布賈姆姆的雜貨店去買零食。走著走著,天空突然下起又大又臭的雨。她已經把所有的零用錢掏出來,想揮霍一下,也不管雨勢,或者晚點回家會不會挨一頓罵。
兩人在偌大的校園行走著。
「阿德,我的鞋子濕了。」
「忍著點,就快到啦。」校園在離市區較遠的郊區,晚上便沒有首都的明亮風光。天很黑,路燈的間隔又寬,均至不得不掏出手機的照明燈領著路走。校園裡臥虎藏龍,樹蛙、白梅花等濕濕滑滑的兩棲動物都在暗處遊蕩、伺伏,只是不特別讓人感覺到。兩個人手勾著手歪歪扭扭的躲避著打落到地上又再反彈起來的雨點,經過一片灌木叢,繞過行政大樓,穿過農學院,才來到文學館後面的小峭壁。
「喏,移動瀑布,只有下大雨的時候才會出現喔。」常德幫均至抹去臉上的雨水,要她睜大眼睛欣賞。
「這有甚麼稀罕的?在我家那邊,這樣的山壁到處都是,比這個大上十倍的也很常見。」她不喜歡看見水流恣意宣洩的樣子。六年前,也是這樣大的雨,她要去布賈姆姆的店裡買糖果,阿莉姊的攤子就在洪流裡被砸成碎片。她被壓在一棵真正的檳榔樹下面,生死皆有檳榔作陪。大人在喪禮前討論立碑的事,又說要不要讓她葬在檳榔樹下,人們一看到就有景物可以弔念。幸好爸爸反對:檳榔樹不遮蔭也不牢靠,要是哪天又來個土石流把樹吹翻了,讓她再受苦一次?出殯那天,母親不讓均至參加,要她在家裡幫忙看門,斜對家的勇凱還坐在機車上抽菸。鄰居雅琴要來找均至玩,遇上勇凱哥便笑嘻嘻說:「勇凱哥!怎麼不去找阿莉姊?你不是最喜歡找她摸奶?現在隨便摸都不用錢了。」勇凱惡狠狠地瞪著眼睛,盡吸一大口菸把氣全吹在雅琴臉上,作勢把菸蒂頭扔來。「伊娘的,誰說我找她?」雅琴躲進均至家,對外面火熱的太陽吐了吐舌頭。均至困惑地問:「他真的不去看阿莉姊?我還以為他愛她呢。」雅琴豎著兩根手指在她腦門旁比一個「妳白癡噢」的手勢,說:「別天真啦。他只愛阿莉姊被摸的時候驚慌失措的樣子。現在阿莉姊永遠睡著了,不慌張,勇凱就沒興趣了。」
這是真的。阿莉姊天生就有種大驚小怪的氣質。勇凱哥的車常常停在她的透明檳榔攤前面,她就一天到晚俯進他的車窗哎呀呀的叫,好像被車子卡得不能動彈似的。均至常覺得,要是她好好發揮天賦,去馬戲團當小丑,人生應該可以得到很多掌聲的。可惜她住在人口稀疏的部落,來來往往的砂石車都很吝嗇。但她是特別慷慨的人。除了洗澡睡覺以外,阿莉一天大概有十六個小時都是個盡忠職守的展品坐在透明的小檳榔攤裡,誰要是寂寞誰就能找到她。她給那麼多男人帶來快樂,如今死了,卻連勇凱哥都不承認他對她的愛。父親去幫忙驗屍回來,只嘆口氣說:「檳榔根淺,賣檳榔的女孩也注定命薄。」
不想阿莉了。常德的手勾上均至的腰。
「妳真的不喜歡瀑布啊?不喜歡,我再帶妳去別的地方。」
「別走太遠,等一下認不了回去的路該怎麼辦?」
這回常德沒答話,只顧著推著她向前,令她有點生氣。均至不是文學院的人,這一帶她不甚熟悉。旁邊立著的蔣公銅像也是頭一次看見。常德帶她走上文學院的階梯,階梯上是一個中空的庭廊,再往內走竟然還有個小花園,邊邊立著一座中國古典式小涼亭。
「我們來避雨,妳把鞋子曬曬好不好?」均至鬆懈下來,把腳丫子從悶濕的球鞋抽出,又任常德一個勁把均至抬放到腿上,從後面摟著,「怎麼啦,都不說話?」
「沒甚麼。說不上來的悶。」
「下雨天,當然悶。不過,我知道悶的時候怎麼樣可以馬上好起來,妳要不要看?」常德矯捷得很。把她放回旁邊的位子,就喀啦喀啦站起來,像機器人那樣一個關節接著一個關節移動。腳踝、膝蓋、胯下、腰、胸部、脖子、一直到舌頭、眉毛,都好像是各自獨立、長在不同人身上的器官。「動一動,跳跳舞,讓身體展開來,馬上就會快樂了。嗯?笑甚麼,不相信啊。」常德要拉她起來,均至卻只是笑,沒有要跳舞的意思。
「阿德,你學舞的人,怎麼會喜歡我?」
「喜歡就是喜歡啊,跟跳舞有甚麼好衝突的?」
「不知道,我只是覺得,你們重視美感,身體的曲線,肢體語言……這些我都沒有。」她的眼睛黯淡下來,「我不是那些打扮得光鮮亮麗的人。」她不是沒有想過要化妝、保養,凸顯女性特徵。但母親給她教訓過,阿莉的專長她都不能學。她甚至最好不要在任何場合提到她,包括日記。阿莉死的那天均至在日記上緬懷她,寫說阿莉這麼早就死了,她都還沒機會向她買檳榔呢。母親偷看了之後氣得把她抓起來,在她屁股上重重打了三下。均至不甘心:「妳說女生的屁股不能給人家碰的。」母親卻冷眼。「妳要學阿莉,喜歡檳榔,我現在不揍妳,難道看著妳屁股以後給更多人碰!」從此以後,心裡的話,均至下定決心不跟母親說。家書都是寫來做做樣子的。也許,真正的秘密是無話可說的。
常德是不是真的喜歡時髦的女生?他聽完問題,竟然沒有回話,只是把她拉近一點。兩隻黑洞那麼幽深的眼睛盯著均至惶惑的眼睛。太近了,均至已經可以呼吸到常德的口氣,好像他們是使用同一套循環系統的連體嬰。常德把兩隻手輕輕放在均至的脖子上逐漸向下,用最擅長的肢體語言說明了接下來的故事。他的一個動作接著一個動作,像極其緩慢的一份邀請,像他慢拍子的舞,專注、獨立、甚至抽離人類規矩。
一排扣子遠離開來。胸罩後面的鉤子也解散了。常德微笑直視她的眼睛,慾望透明像雨水,打在身上不痛,卻叫人打從脊椎發冷。均至顫抖地說:「這裡是公共場所,太危險了。」常德則安慰她:「不要擔心。會在這個大雨天出門還走到教學區的,只有我們這兩個小瘋子。」他的手熟練得像製麵師傅那樣在她隆起的乳房上頭搓揉,也不急躁。像桿一塊生的麵團,均至初初被聚攏,任何的注視跟觸碰都很陌生。風從解開的扣子微微拂過身體,她不由得打了一個哆嗦。常德的手移動到下方,一把火彷彿從她軀幹的最下端燒灼上來。她肯定是裡面包著甚麼紅豆或者巧克力那種餡料的麵包,撕開來會爆炸的。他推移她,亮出那把又長又利的劍。均至閉起眼睛,想抽開思緒,幻想自己已經回到房間。卻又看見常德是那個把一顆一顆泡泡捏破的人,她則是那張泡泡紙,從本來豐腴鼓脹具保護力的軟墊,削減成一張單薄的塑膠片。她害怕,自己真的變得跟阿莉姊一模一樣了。
「妳心跳跳好快。」常德想溫柔的說,卻難掩興奮。
均至沒有領情。「對!怎樣?」粗魯的口氣把常德嚇一跳。
「怎麼了?妳想不想也摸摸看我的心跳……。」
「摸你的心跳?你當我是甚麼,絨毛玩具嗎?為什麼我們要摸來摸去的?而且,你甚至沒有問我沒有想過我的感覺!」均至沒有摸他,她重重推了他的胸口。常德頹然坐著,滿臉疑惑。「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就像一個小孩喜歡小狗,他就會想走過去摸摸牠的毛髮、搔搔牠的肚子、拉拉牠的尾巴……。」
「去你的。我才不是狗。你才是狗!你才是狗!」
均至的眼睛像檳榔那麼紅那麼圓,瞪著他。
空氣中一陣靜默。
「不喜歡我們就不要。」常德道歉,然後把火吹熄,摸著她的頭髮,讓她貼在他的衣服上。
但他們還是被逮住了。
腳步聲輕輕傳來,從蔣公銅像的腳下。均至說有狗就有狗,一隻又一隻,搖著尾巴、發著低嗚聲的黑狗從暗處來。那些狗有森森的牙齒、反光的瞳孔。牠們望見她坐在常德的膝上,露出的半截屁股。有的甚至還看見她象牙白的乳房。而又是這麼大的雨,狗群全想進來涼亭避避難。常德幫均至扣扣子,有點慌亂:「快把褲子穿起來。」她坐在他腿上不得不從命,並感覺母親正透過狗群的眼睛注視她。全都髒掉、臭掉了。她恨恨地想,她討厭大雨把鞋子弄濕,更討厭常德命令她穿褲子把內褲弄濕。
哪裡的狗都是一樣的,首都的狗看起來也跟村莊的狗一樣飢餓。這種眼神均至牢牢記得。十八歲的均至記得十三歲的下午,她成功到布賈姆姆的店挑選完大把糖果後,天完全黑了。布賈姆姆把鐵門拉上,準備看七點的新聞,因此沒有多送她走一段路。她一手拎著糖果,一手撐傘,在那條泥濘的路上突然覺得好懊悔。不,事實上是覺得有點怕,因為從布賈姆姆的店回家,要經過一個巨大的垃圾場,村狗正從巷子的兩個方向要回牠們的狗窩。牠們看見均至,就露出那種晚上要加菜的表情越走越近,吠叫起來。時間不早,母親在中學已經改完學生的作業簿,要準備回家開飯,若均至來不及在母親回家前坐到書桌前,肯定會挨一頓揍的。「布賈姆姆!布賈姆姆!」均至慌亂中想找救兵。她聽過村狗咬人的故事,知道自己要逃命。但反而,經她一喊,狗群更加激動,其中一隻,可能是牠們的領頭,以飛奔的速度向她的腿撲過來。她驚叫一聲,把手上的糖果遠遠扔出去。不要了,糖果我不要了,花我所有零用錢買的,不要了。但狗群不想要糖果,牠們嗅聞著均至的裙襬下緣,想掘出所有秘密。
不可以驚慌失措的,她提醒自己。在垃圾場的角落,她盤算各種選擇:可以試著攻擊那些狗,把牠們嚇跑。她想扔擲書包裡的鐵製鉛筆盒、國文課本、數學課本和厚厚的參考書,讓文明的力量在野性前面發揮嚇阻效果。如果嚇不倒,反正她也把文明都丟掉了,乾脆就像個野人用雨傘跟狗群決鬥也可以。其中一隻白黑相雜的狗突如其來的又用前腳去勾她的制服裙。濕軟的泥土在她的小腿和裙子留下印記,她沒辦法克制的尖叫一聲,連忙把後背包扯下來擋在腳邊來回甩動,另隻手因為拿傘,根本空閒不下來,沒法把拉鍊打開把書扔出來。
一定得突圍。少女均至不管淋濕不淋濕,總不能停留在原地等著被圍剿。於是把雨傘傘面垂直地面方向,盾牌架式,往家的方向衝去。狗從後面追上來,用爪子撲抓她的屁股。大雨把路淹得泥濘難行,她邊跑邊哭,想到回到家要解釋的這一連串難堪跟將挨的棍子、丟失的那整袋沒有開封的糖果、還有後面追逐她的這群獠牙猛獸,便不知道要繼續奔跑還是乾脆停住。反正不管往哪個方向都是沒有盡頭的恐懼。
她不知道跑了多久、跑得多快,快到狗群終於都迷失在大雨中沒有跟上,均至才彷彿從一場惡夢醒過來。只是現實也下著雨,外加從玄關衝出來也淋濕了的母親。媽很是激動。家的一切原來都很滂沱很脆弱。她看見女兒大腿上的抓痕跟裙襬的汙泥,又見她怯怯不敢進屋的模樣。「是誰?誰害妳這樣?把那個傢伙揪出來,我們告他,看他怎麼還我女兒一個清白……。」媽走近,哭了,她連跟爸爸吵阿莉都不會哭的,看見均至竟然哭了。「誰叫妳放學不馬上回家?颱風天妳不知道嗎?外面多危險妳不知道嗎?我怎麼教妳的,枉費!妳快跟媽說是誰,村子的人躲不到哪裡去,妳快跟媽說是哪個壞蛋……。」均至才坦承:「媽,不是人,是狗……。」
「是狗,不怕的。」常德拍拍她的背。正如當年母親一顆緊繃的心竟然就這麼鬆弛下來。他們把狗的突擊想成偶發事件,壞又怎樣?那麼矮的生物,也就沒甚麼好想,沒甚麼好計較。只有年輕一點的女孩子懂得狗的可怕,她們知道自己的秘密會被看穿。當狗群在她下體的高度隨意衝撞,能嗅出一股不同的氣味。那裏不是沒有甚麼,她正流著血,初經或者常德惹的禍。牠們提醒她是個會流血的女人,牠們提醒她成熟後時時要面臨被圍困的麻煩。已經不一樣了。十三歲那天她跑回家的時候,突然好想把帶血的內褲脫下來丟得遠遠的,像甩掉糖果那麼乾脆。她很意外狗群怎麼會追到一半就消失了?後來才知道,黑狗部隊全跑去找阿莉。坍方的土石周圍,爸爸說,遠遠可以看見十幾隻黑狗部隊不斷想把石頭咬開,要把碎石跟玻璃片下的阿莉拖出來。若不是狗的功勞,大家也不會這麼快發現阿莉抱著年幼的孩子在血泊之中,沒有閉上眼睛的臉。
村人都說阿莉會變成厲鬼,因為她的屍首被發現時還套著低胸露腿的紅色性感洋裝,彷彿等著誰還要來買她的檳榔。只有均至不相信。阿莉是那個把狗引開,救她的偉人。就算變成鬼也是很善良的那一種。每次下起大雨,混著狗吠聲,均至就沒有辦法忘記她。她知道給母親的家書要寫些甚麼了,反正母親現在的棍子也打不來台北,她得豁一豁。這是個很大的雨天,大雨把她隔絕在涼亭裡,只有狗和男人作陪,除了阿莉沒有別的人可以理解。她想到阿莉還活著的時候,她們唯一談話的經驗。那是大豔陽天。均至和朋友打賭輸了,必須一個人從山上跑下來去大馬路邊向她討檳榔吃。錢掏出來了,阿莉卻不給。「妳偏心,為什麼就可以大大方方賣給男人?」她永遠記得那一幕,阿莉在大太陽下亮著閃電般的黑眼睛。很認真的說:「檳榔很傷身。我只賣給欺負我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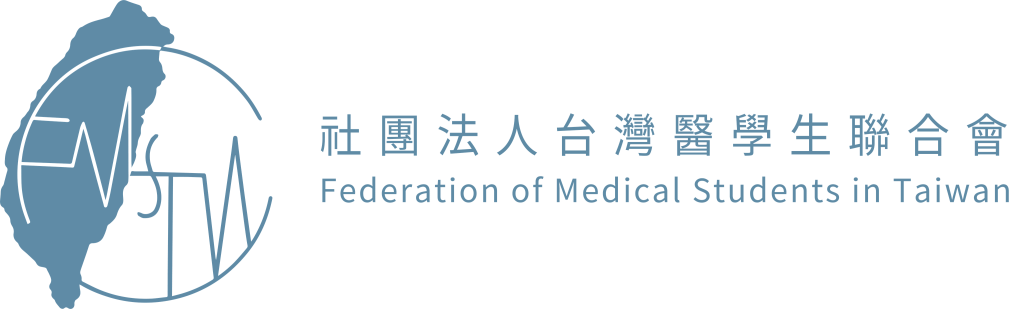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