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屆散文組佳作]台大醫學二-何奕儒《毛毛蟲》
一條嫩粉的毛毛蟲在肉色低窪處靜靜淺眠。八個月來,它幾乎總是這樣睡著,淡淡的,穩穩的,彷彿無關痛癢。
而實際上,一直以來,疼痛與之俱存。
短暫,細微,且無跡可循。
獨獨我一人感受,但並非獨自承擔。每當它翻滾、折騰,引起一陣微弱的抽痛,包容我的小小世界中,貼近的人們,彷彿被狠狠囓咬一般,眼淚隨之而來,但鮮少被看見。包容我的小小世界待我一向溫柔美好,沒有疼痛的必要,更沒有憂傷的餘地。
獨處的時候,我接納、包容它的一切。鏡子裡,伏臥於下頦凹處的它,毫無傷害性,溫順地睡著。料想它應當對於自身處境毫無警覺,酣然而眠,一睡,就是半年一年之久。周遭異於往常的眼光絲絲射入,同情而銳利。
究竟該怪它什麼?只不過是挑錯了地點,擱淺於不得當的位置,正吸吮著夢境的它,渾然不覺於本身的存在是如此明顯而無辜的罪孽。
它生得甚醜,粗粗短短的體格,頭部過大,尾部歪扭曲折,外層裹著粉嫩剔透的皮膚,皮膚之下,隱約可見發腫的血管,如漆紅的荊棘竄流。整體看來,如同被扒光了皮的畸形物種。好在它體態小巧,醜得玲瓏,醜得輕盈,尺寸被整型外科的軟尺精準測量過,長、寬、高各是三點五、零點五、零點二公分──這是它三個月大時的體型。醫生說,大小應該不會再變了,但顏色還會退,必須等。
也好,繼續等,我才能繼續琢磨與它相處的時光。
細數從頭。七月半的烈陽下,無預警地,它出現。我細細密密予以呵護,白天防曬,夜晚防寒,外出時用透氣膠帶層層貼牢,再覆上抗紫外線口罩,萬無一失;晚上我蓋被,蓋的是棉被,它也蓋,蓋人工膠布──含有矽膠成分,據說能抗疤──密密實實,封住它的睡眠。
期間,不斷有新面孔與它照會、新的指示必須被遵從,我都聽,照著做,摸透它發作的時機,並與我發作的情緒層層對應,費了極致的耐性和平共處。激烈的光景通常興於夜半,不動聲色地它宣洩於針刺般的難受,而我以安靜的眼淚濡濕一枕無眠的夜晚。
新生的兩個月,變動最大,它從一窪平坦的靜水長成現在這副德性。原先平滑的深紅色膚塊日益凸起,從下頷凹處伏升。我不甚在意,老爸卻看得心驚肉顫。於是,九月中旬,我們再度回到醫院。
──日日煎熬,最親近它的莫過於我,最在乎的卻是老爸。老爸不願正視,而它亦習慣杵於老爸畏縮的目光底下。看著我的時候總不免掃見它,那些時刻裡,我佯裝鎮定望著老爸飄忽不定的矛盾,而令人失望地,視線總在接軌之前,無力垂墜。
感覺就像是,老爸不願意正視我一樣。──
診間裡,照慣例,記錄了它的成長。幾個月來身形日益臃腫,且逐日染上肉紅的血暈。醫生決定為它訂製新衣,一只膚色的彈性頭套,依照我的頭型剪裁,能牢固地將壓力集中於它的軀幹。天天壓,效果可見。
「睡覺的時候戴,受得了的話,白天也戴著。」甭問,當然受不了。無法想像旁人將怎麼看待這件新衣,一一纏上的眼神也許是同情,也許惋惜,也或許只覺得鋪張得可笑。
「我們不知道能夠幫助多少,但是,這些事情,做了總是好的。」
醫生不斷提到「我們」,診間裡有我、疲倦的老爸、醫生和它。不知道他究竟是指哪些「我們」。
夜裡,我們聽話地戴上新衣,等待變動降臨。夏夜燥熱,偶爾,睡前妥當戴上的新衣,醒來時卻不在頭上,隱約知道夜半裡做了夢,夢見惡鬼一面嘲笑我戴的肉色內褲,一邊使了詭計逼著我摘除。我歸咎於「它」──被迫著衣的它,化身惡魔,將淺眠融入我的睡眠,使盡伎倆,擾亂計畫。
老爸發現後,只問我一句:「為什麼故意這樣做。」
某天夜半驚醒,瞥見半掩的門口老爸的黑影,才知道他鎮夜無眠,看守我,與我的頭套。以愛之名他選擇了無聲的守護,對女兒的疼惜化為無限延伸的藤蔓,攀入我的生活與夢境。
他的眼神是憂傷,無名、不可理喻,因此我拒絕回應。
初時我們在交談時避開「它」。後來,我們避開彼此。
夢裡,它開始遷移。這次,挑個隱蔽的藏身處吧。我這麼建議。它順從地離開低窪的窩巢,奮力蠕動於肉色泥淖,漫無目的,經過了頰的田野與眉的山丘,曲折穿梭於髮際,最後,輕輕地停駐在太陽穴旁不起眼的位置。黑暗中,我噤聲等待。移動的痕跡冰冷而濕黏,一路延著臉頰流淌而下。
驚醒時,下意識摸了下巴。下頦凹處的柔軟窪地,爬滿了未乾的水痕,而它正安穩地睡著。
關於夢,我一個字也沒有向老爸提起,關於它也一樣。
獨自一人,老爸搬進了名為悲傷的國度,陌生而遙遠,我找不到相通的語言。
某次回診,在醫生和「我們」面前,老爸的眼淚像針,從破裂的深甕底部滂沱宣泄,扭曲的面容暴露了他積壓的自責。在脆弱的老爸面前,我以為自己能以眼淚相伴,並順勢敲碎荒唐的冰牆,但那一瞬間,恐懼佔據一切,當下,我情願遠遠等著,束手無策,等待眼淚收乾,等待世界被包裝回它該有的樣子。
任性的我以憤怒彰顯滿腹恐懼,天真以為老爸能理解並體諒。
但他落入沈默的牢。
「只要你不覺得我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沒有難過的必要了啊。」我以蠻橫對抗他的緘默。
當然,誰都看得出來,的確,我不一樣了。但我平心看待,老爸卻無力掙脫。一場暴風雨催得太倉促,父女被淋得渾身濕漉,強勁的雨勢中我悶頭衝回安全的庇護,留下一向堅強的老爸,沉沒於無盡的沉默。
毫無立場怨懟他的過分在意。一場意外裡,我只是我,而他是我的父親。
寒假去了台東,回到一年前曾經服務過的排灣部落。久未見的孩子撲向我,劈頭問我怎麼了。「姊姊我太不小心,出車禍啦。」我抱起身旁的孩子,輕描淡寫地如同當時無雲的天空。「可以摸摸看嗎?」懷裡的孩子伸出手指,碰了碰它。柔嫩的指腹小心翼翼地吻上它畸形的孤獨,指紋脈絡毫無惡意成份,對他們而言,純粹是場新奇的小冒險,單純而無知。它一如往常的淡漠並未讓童稚的好奇心減少分毫,熟悉的孩子們紛紛湧上,快樂地喊著:「姊姊,我也要摸摸看,輪流,輪流!」我被眼前乍起的歡騰逗樂了,順從地俯下身子,接受孩子們儀式般的莊嚴觸診。
「哇,真的耶!軟軟的,好像光溜溜的毛毛蟲喔!」
晚上我躺在台東的星空下哭了。朦朧中幾顆流星劃過,獨自一人,宇宙寂靜見證。
那是我第一次看見流星,並且安靜地接納隨之而來的悲傷。與它共存的日子裡,生命輪軸持續滾轉,一斑污濁的印痕被軋在來時的輪跡中,不再消失。
空虛、惘然、疲倦、焦慮、自卑、自厭。輕微,但都足以在情緒汪洋中佔據一角。漸漸習慣淡然於外,聚焦於內,視線反射,停駐於內裡深層之地。自我對白時,就像縮為一團不分裡外的圓,又好像,頭顱被無名的力量狠狠朝下顎收攏,腦中雜音順勢納入胸口,於是,汩汩川流不再單純敲響生命的節奏,更象徵情緒。愈縮、愈緊,愈緊、愈靜。有時候,發現得太晚,我已溶為一灘寧靜。
我掉進洞裡了。總是如此形容那些時刻,那些時刻裡,世界於我無干。
只想安靜地告訴自己,告訴老爸。一切都沒關係了。
八個多月過去,它不再改變而我不再哭泣。摘下頭套,不在意了。我歸還它安穩寧靜的睡眠,它還我不受攪擾的生命。
很多人問過我,事情究竟是怎麼發生的?說實在,我不太記得了。醫生說,片段記憶會慢慢回來,沒回來的,或許本該被遺忘。
那是個平凡的七月天,天色濛濛亮,我和老爸已經抵達陽明山半腰。第一次嘗試騎單車爬坡,幾百公尺的坡段,騎起來比想像中困難許多。扶著嶄新的單車,一面喘,一面聽老爸絮絮叨叨地講解齒輪的運作、呼吸的調配、身體重心的擺放等等。「待會下山需要技巧,記得,隨時按住煞車,一點一點放掉,車速絕對、絕對不要快,第一次都會比較不習慣,慢慢來,我在後面跟著。」
在那之前,父女之間並不特別親近。單車與馬拉松把我們牽在一塊兒,老爸陪我練跑、教我關於騎車的一切,我們熱愛相同的事物,汗水淋漓地共享疲憊與快樂。擁有老爸的強力支持,我毫無後顧之憂。
難以形容這種幸運。
「出發吧,該回家了。」
延著下坡,乘風而行,老爸在五公尺後跟著。晨光融入微風,撲個滿懷,皮膚被清新的空氣浸潤,耳際柔軟的風聲不止,除了指頭為了緊壓手煞車而感到些微痙攣之外,我無法不讚嘆當下的一切。
世界輕柔而美好,彷彿一場美夢。
醒來時,我在救護車上,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虛,舌頭麻麻的,空空的,「我牙齒好像不見了。」終於發現空虛感的源頭,我以為只是心中的喃喃讀白,但老爸的聲音卻細弱地迴旋:「我知道我知道,沒關係,牙齒都可以補,沒事的,沒關係了。」方形的空間疾速前行,晃盪不止,響亮的鳴笛彷彿隨之震顫,模糊中,看著老爸低垂的後腦勺無意識般地搖晃著。
倏地,覺得下巴一陣刺痛,像一桶冰水從天而降,唰,疼痛淋遍全身,一陣,一陣。
再度醒來時,在急診室。門牙的空洞以紗布填塞,而下巴挫傷,整塊皮都不見了,無法縫合,醫生只能稍微清潔,消毒,再用紗布輕輕地罩住。
一條嫩粉的毛毛蟲,便是在那個時候鑽入紗布,靜悄悄地住下來。
心裡仍淺淺地相信,終有一天,羽化的好時日,它將突破肉繭,如同來時一樣不著痕跡地離去。
而時間繼續走,它以陌生者之姿滲入生命的每一吋。
一晃眼,我們都已不再是最初的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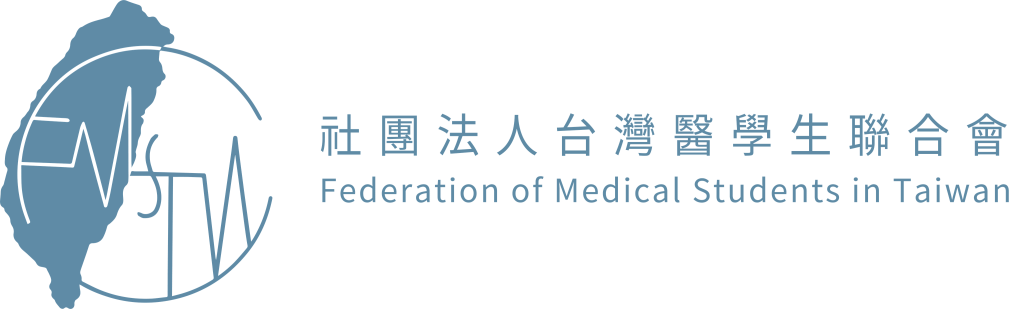
發佈留言